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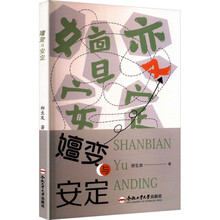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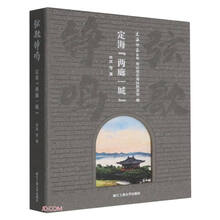


《E·B·怀特随笔:重游缅湖》作者E·B·怀特(1899—1985)是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随笔作家,作为《纽约客》主要撰稿人的怀特一手奠定了影响深远的“《纽约客》文风”。怀特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关爱,他的道德与他的文章一样山高水长。除了他终生挚爱的随笔之外,他还为孩子写了三本书:《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与《吹小号的天鹅》,同样成为儿童与成人共同喜爱的文学经典。《纽约时报》为怀特逝世发表的讣告中称“如同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样,E·B·怀特的原则与风范长存”。“E·B·怀特随笔”由作者本人选定,囊括了这位最伟大的随笔作家那些最伟大的随笔,中文版分为两卷出版,名曰:《这就是纽约》与《重游缅湖》。
佛罗里达珊瑚岛
1941年2月
我在佛罗里达一处珊瑚岛的海滩别墅写下这些文字。外面,风雨敲打着汽车。西来的暴风雨掀动翻滚的大浪扑向海岸,惊涛阵阵,持续的轰鸣声代替了往日间歇的拍打声。商会出于好心,对此喧嚣视而不见,埋头起草下星期在展馆的时装展公告。报纸上说,明天天气好些。
别墅的墙壁是用企口板横向拼成,漆成绿色。地上铺草席。草席下有一层细沙,是进门时趟入,又渗到草席下。我本想揭开草席,把沙子撮成一堆儿,倒出门外,终于还是作罢了。显然,珊瑚岛上一向是这般情形,我没有理由横加干涉。屋子角落的一处小小的木制基座上,摆一台煤气取暖器,靠屋子附设的储罐供应煤气。这台设备可将空气中的氧转化为热,迅速提高室内温度。点不点取暖器,全看你是想在通风良好的屋子里冻僵,还是想在温暖中窒息。操作几回,就能找到巧妙的平衡——留下足够的氧气维持生命,又能产生足够的热,免得冻死。
西面的墙上,挂了一张印第安壁毯,壁毯的一侧,别了一枚圆徽章,上面的文字说明了它的来历:卓普俱乐部青少年培训课程。北面的墙上是有凹斑的柏木壁柜。最上一层,摆放了三只大松果,两只涂成翠绿色,另一只涂成砖红色。还有一个罗马双轮战车形状的镀金烛台。下面一层搁板上有一些贝壳,有人下了很大力气,让它们看上去像是飞鸟。最底下一层,站着一只小不点儿玩具牧羊犬,用野兔皮制成,舌头用红法兰绒。
我坐的地方再往前,是厨房,有煤气炉,还有一台年头很老的小电冰箱。冰格留下深深的刮痕,想必是人们为了撬它下来,使用了起子、刀子、改锥,连带上气急败坏。冰箱突然启动时,声震屋瓦,各处的灯光瞬问都黯淡下来,随即重放光明。冰箱里放牛奶、黄油和鸡蛋,供明天早餐之用。明天早上,还有牛奶送来,我再留给次日早餐,如此一来,我每天喝的都是头一天的牛奶,从来享用不到完全新鲜的牛奶。假如我索性扔掉整整一瓶牛奶,本可以避免这种局面,但当今世界上,没人能如此大胆。扔牛奶是一宗罪,我们都很清楚。
厨房和卫生间水龙头流出的水含硫,不适合饮用。它在下水道周围留下深棕色的污渍。蘸水往脸上抹剃须膏时,感觉就像用细砂纸打磨下颚。水质太硬,含硫量又高,一般的肥皂都不管用,刷洗早餐的碗盏时,非得用德夫特牌强力洗涤剂。
房舍的门廊处,有两个细颈玻璃瓶,分别立在各自的架子上,里面装了泉水,供饮用、煮咖啡、刷牙。水瓶和架子的押金是两美元,每瓶水五十美分。两家相互竞争的公司为社区送水。我不巧与这两家都有点瓜葛。每两三天,这家或那家公司的人就会光顾,盘桓一会儿,嘀嘀咕咕地抱怨门前对手公司的水瓶。我曾试图退掉一家公司,保留另一家,而这得有点说一不二的本事,我偏偏没有。让我惊讶的是,一个人喝光十加仑水,需要多长时间。我本以为,用现在的一半时间就尽够了。
今天上午,我从报纸上读到,一位老黑人,一百零一岁了,自夸他一生喝下过多少威士忌。他说,他曾在酿酒厂工作,每天,他们给他一加仑威士忌带回家,上班的这几天一切都很妥帖,但到了周末,他说,他就得自己买上一加仑酒,帮他飘悠到星期一。
厨房的碗柜里,有一袋橙子,早上用来榨橙汁。每只橙子上都贴了“添加色素”的标签。给橙子染色,使之呈橙色,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无耻的举动。这简直可以说得上骇人听闻,这番举动,显然是在暗示大自然不知道它该做些什么。我觉得,染成橙色的橙子,同涂成绿色的松果一样让人反感。我认为这是我见到的最丑陋的事情,似乎很难相信,这块地方,或许吧,在果树林子十英里范围之内,我买不到没有给人染色的橙子。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这样想,欺诈已经成了一种国家美德,在许多圈子里为人津津乐道。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我从晨报中得知,已有一百j十六车橙子装车启运。如今,可能有数百万儿童不清楚天然橙子为何物——只知道人工染色的橙子。倘若他们看见一只天然橙子,只怕会觉得怪异。
镇子里有两家电影院,靠一座桥与珊瑚岛联通。其中一家影院,允许有色人种坐在楼厅。另一家影院,根本不允许有色人种进入。某日,我看过一个宣扬爱国主义的新闻片,最后是美国国旗在微风中飘动的画面,还有一行字:不可分割的国家,人人享有自由与正义。观众掌声四起,但我判定,在这个禁止黑人进入的影院里,不能为(人人享有的)自由与正义鼓掌。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心目中人人享有的自由与正义,不过是为他本人和他的朋友所设。我坐在那里,悬想如果跳起身来,大喝一声:“你们这帮人如此喜欢自南和正义,为什么不许黑人进入影院?”那会有什么后果。我敢保证,每个人都会大惊失色,这是我很想做的事情,但始终没去做。假使真的做了,我想影院经理会抓住我的胳膊,轰我出去,理由是影片播映时分,宣讲自由妨碍了安宁。人在南方,必须得照南方人的规矩办事,但我虽然愿意管我太太叫“小鬼头”,却不愿意管黑人叫“黑鬼”。
北方人很可能认为南方人在种族问题上偏执,南方人却认为北方人脱离实际,说出话来往往靠不住。黑人差别待遇的理念让北方人不满意,但在黑人人口与白人不相上下或多于白人的城镇里,却被视为合情合理。对一个问题,答案是切合实际的,还是理想主义的,要看人们回答时,说的是一年,十年,抑或是一百年。换言之,完全可以想象,即使目前的限制不会很快取消,一百年后,黑人也必将享有更多的自由。但这并不足以让今天的黑人观赏海蒂·拉玛尔。
想到南方在颜色问题上,态度如此前后不一,我不禁哑然失笑:有色的黑人不得进人影院,“添加色素”的橙子则大受欢迎。本州这一地区的某些城市举行游乐会,缅怀以往,鼓吹未来,我在自己的脑海中,设计了一辆彩车,希望将它驶入游行队伍巾。车上一位曼妙的黑人女子,与其他人浴的美人同行,身上印了那神气的字眼儿:添加色素。
隔壁的房子里,住了位太太,是个狂热的孤立主义者,她不断跑出跑进,手里拿了小册子、书籍和作了记号的报纸,试图说服我相信,美国应当只管自己的事情。她除过思想,还带来了沙子,我得跟在她身后,每天打扫两三次。
今年,佛罗里达抱怨生意不像平常那样好做了。他们告诉你,工业的迅猛发展导致了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北方的工业巨子忙得没时间晒太阳,甚至顾不上坐在亚热带的别墅里看看雨景。迈阿密额外拨出数以千计的美元做广告,指望引诱行政官员撇开国防计划,享受一番黄金时刻。
虽然我不是考古学家,但我喜欢佛罗里达,喜欢它那些未曾完工的城镇的遗迹,一如喜欢它海滩上明媚的小屋。我喜欢顶了正午灼热的阳光,漫步在死寂的人行道上,人行道通往生机盎然的丛林,甘蓝棕榈在半途而废的街道上投下刺状阴影,藤蔓错杂,纠缠路边古旧的砌石,像在狂热地拥抱,反舌鸟沉浸在旧日不动产鼎盛时期的辉煌中,鸣啭不停。复归自然的林荫道最动人心魄,它散发一股奇特的气息,预示着什么,等待未来的世纪,那时,鸟儿,还有蜘蛛和疾行的小蜥蜴,都会恢复记忆,而如今,它们正在一度寄托了人们梦幻的平坦、坚硬的大地上烘烤自己。沿着这些笔直的步道,生长中的森林渐渐杂乱,不再对称——和悦而又随意的大自然将成排树木的线条变得柔和起来,路面上初生的表土滋养生命,路面的裂隙给草茎盘踞,引种的藤本植物荒芜了,明艳的花朵恣意开放,头顶,红头美洲鹫平展双翅,在清朗的天空中飘摇,等待木槿、丝兰、千手兰和棕榈丛中哺乳动物的死亡时刻。我记得那些热闹的日子和彩虹尽头的迷离梦想,钉了挂图的办公室;挂图上的标示;乐队演奏悠扬的乐曲,抚慰漂泊者面对郊区住房的神话时不免恍惚的灵魂;彩虹起点的免费汽车服务;树荫下小桌上供应的午餐;吹人欲醉的熏风;合同上签字的虚线;签名;预感带来的惶恐,以及佛罗里达苍天上飞翔的美洲鹫。
我喜欢这些尚未发展起来的城镇,它们始于贪婪,经过一番仓促规划,到底没能兴建起来,给人去糟蹋,这些还残留希望的城镇,没有给染上霓虹灯和种种污秽。我也喜欢建筑群落之外的海滩,那里还是野性的,天然的,鹬鸟来此落脚,一阵浪涛涌来,连忙退避,像小孩子一样,有时,臀部一翘一翘的乡下妇人在这里拾贝,还有时,老兵会来掘斧蛤,给他留在露营拖车营地的饥饿的老伴享用。
大海的涛声最能消泯时间的概念。你闭上眼睛,倾听海的声音,多少个世纪一涌而过,大地又绿了——一个方生的青翠时代,海与陆地刚刚接触,彼此相识,不过几十亿年的时间,软体动物刚开始进入浅滩蠕动;现在,人这种懦弱的家伙,躲在遮阳伞下,身上涂了防晒油,戴上他的偏光墨镜遮挡光线,在温暖的沙滩上铺好浴巾,舒适地摊开长长的棕色躯体,侧耳倾听。
大海能回答所有问题,总是用同一种方式;你若读报纸,报上满是无休无止的讨论、争吵和骚动,还有分歧、重大决定和协议、计划、方案、恫吓和反恫吓,于是,你闭上眼睛,大海送上又一波浪潮,自从有了世界,大海就一浪追着一浪,绵绵不绝,它抚平了一切,又打碎了一切,去而复返,飞溅的浪花中,你能听到它说:“就这么快吗?”
……
——《纽约客》前总编威廉·肖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