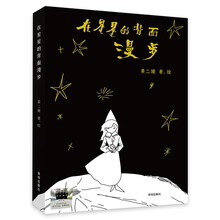但我们也很容易看到他的踟躇。自从凯末尔主义以来,土耳其一直明确地把自己确定为一个世俗社会。但由于近年来土耳其国内重返伊斯兰的呼声日高,世俗政权在屡遭欧盟拒绝之后也日益倾向于在伊斯兰世界寻求自己的文化亲缘,亨廷顿甚至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预言:“在未来某一时刻,土耳其可能乐于放弃它像乞丐一样恳求加入西方的令人沮丧和屈辱的角色,恢复它作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主要对话者和对抗者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高雅的历史角色。”。面对土耳其国内的意识形态压力,在表达坚定的世俗立场的同时,帕氏不得不为自己设立一些巧妙的辩解——这成就了文本的优雅而狡黠的含混——比如,他反复公开宣布该小说最大的目的是为了向细密画——伟大的伊斯兰艺术致敬。但我们知道细密画其实不过是一层精巧的薄幕,它本身不能作为文本强大的目的和主题;又比如,在描写细密画派的大师对于安拉信仰的忠诚,和描述世俗的、令人激动的透视法带来的个人与世界关系的革新时,我们读到了同样的真诚。这种真诚,并非所谓的“对于两种文明调和之期待”——大部分调和的立场不是出于天真就是等于没有立场。这种真诚恰恰出于作者的意识形态面对土耳其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带来的压力,而在笔下体现出艺术体操的柔韧,以一种转喻关系,将对伊斯兰文化的信仰与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含混置换。<br> 再比如,也是借一本《历史》书之口,说到在伊斯兰地区频繁的征战中,战胜的国王,作为确立其统治的第一要务,总要立刻入主已故国王的图书馆和后宫。在图书馆里,“老练的装订师拆散了已故国王的书籍,将它们重新编排,开始着手装订新的书册。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