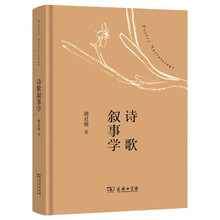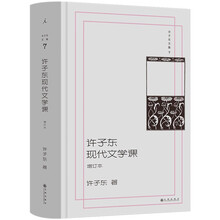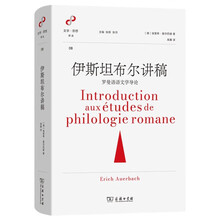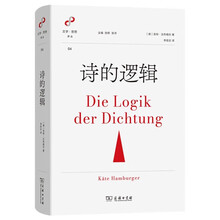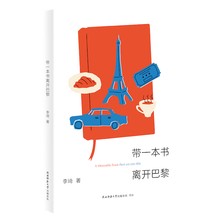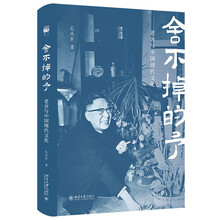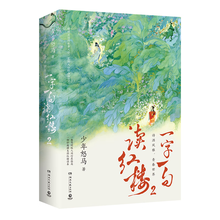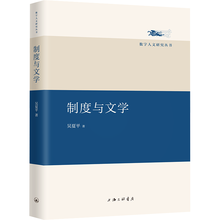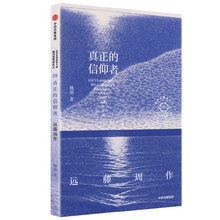第二节 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论争与调和
对学的强调,使得元人,包括由宋人元的遗老,重启“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争端。
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论争,假如从司空图提出这一说法开始,几乎贯穿了我国古代诗学批评史。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论争,首先和主要的属于诗学批评和,诗歌创作的范畴,尤其是唐宋诗之争、之变的过程中的一种理论反映。第二,到南宋中后期,随着士人阶层的分化,尤其是随着科举士人与江湖士人阶层的分化,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论争,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文人和诗人的分野,这使得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多少蕴含了一种身份特征,而有社会学的意义。这里即试图侧重于后者对其做一些探讨,从一个侧面说明由于创作主体的分化,其身份特征的差异,所导致的诗学观念上的差异。
早在南朝梁钟嵘《诗品·序》中,即言:“大明、泰始,文章殆同书抄,拘挛补衲,蠹文已甚。虽谢天才,且表学问。”学问之诗与天才之诗已经异途①,杜甫、韩愈之后,倡导“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则开启了宋人作诗“无一字无来处”的先河。至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乃以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相对待,因此司空图的这种讨论,是随着杜甫尤其是韩愈诗歌在创作方法和风格特点上的大力开拓,逐步引起人们的关注之后开始的,司空图此文,其意不过是对于这些讨论做一个厘清:
金之精粗,考其声,皆可辨也,岂清于磬而浑于钟哉。然则作者为文为诗,格亦可见,岂当善于彼而不善于此耶?愚观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始皆系其所尚,既专则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于不朽,亦犹力巨而斗者,所持之器各异,而皆能济胜,以为勃敌也。愚尝览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为道逸,非无意于渊密,盖或未遑耳。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探搜之致,亦深远矣。
俾其穷而克寿,玩精极思,则固非琐琐者轻可拟议其优劣。又尝铺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历,乃其歌诗也。张曲江五言沉郁,亦其文笔也。岂相伤哉!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词只句,不能自辨,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因题柳集之末,庶俾后之诠评者,无惑偏说,以盖其全工。②
司空图的意思是说,文人之为诗,诗人之为文,都是由其好尚而来的(“始皆系其所尚”),但只要由其所尚而各极其致,都是好的,都可以“炫其工于不朽”,李白、杜甫以诗名,而文似其诗,张九龄以文名,而诗似其文,但两不相伤。他做了这样的比喻,“亦犹力巨而斗者,所持之器各异,而皆能济胜以为劲敌也”,诚然是很通达的议论,而大致仍属于诗学的范畴。此后,宋人如苏轼、刘克庄于韩、柳诗歌的批评,多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来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