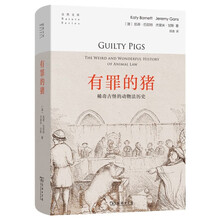导 论<br><br><br>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律体系之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东亚、东南亚地区产生着影响。国内外学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方面,对东亚和越南研究较多,而对于与中国毗邻,有大量华人聚居的东南亚其他地区研究较少。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东南亚具有深远影响,时至今日,已成为东南亚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br><br>一、相关概念的界定<br>(一)东南亚 <br>本书中的东南亚,是指东经92°至东经141°、南纬14°至北纬28°之间的区域,北面连接中国陆地,东临太平洋,南面与西面则为印度洋所环绕。包括缅甸、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十个国家,由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上将这一地区称为“南洋”、“西洋”,而西方人则称之为“印度支那”、“印度群岛”。东南亚地区“被视为一个整体”的历史非常悠久,然而“东南亚”(Southeast Asia)这一现行的国际通用称谓,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时期才开始流行。出于战略考虑,盟军将这一地区统称为东南亚,便于安排与指挥。战后,东南亚主要国家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五国首倡,建立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文莱(1984年)、越南(1995年)、老挝、缅甸(1997年)、柬埔寨(1999年)先后加入,东南亚“共同意识”日益彰显。<br>近代学术界对于东南亚的整体研究开始较晚。“东南亚”这一通用名称出现前的本地区研究,以16世纪为界。在此之前,关于东南亚的文献资料以中文为主。根据不完全统计,从西汉到晚清以前,涉及东南亚历史的中文著作共有274种之多,包括正史、方志、游记等等。对于今时今日的研究者而言,抛开这些文献资料去研究东南亚早期历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东南亚本土保留的关于东南亚的文献资料,在16世纪前,也只有寥寥几部。例如《爪哇诸王志》、《爪哇史颂》等等,这些14世纪之后出现的编年史和其他文学作品也是研究东南亚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br>16世纪,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东南亚,西方学者也将研究的视线投向这一地区。对于东南亚地区的研究,首先表现为对本国殖民地的区域研究。学术与政治从来就不是完全脱离的,学术无国界,学者有国籍,对本国殖民地区更为关注也属正常现象。东南亚地区以殖民国家冠名,被分割成“英属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国家的制度文化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例如,F.W.斯塔普尔的《荷属东印度史》,就是以东南亚地区荷属殖民地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一部荷兰人眼中的东南亚史。在国别研究之外,也有重要的综合性研究著作。乔治•赛岱斯在1944年出版的《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国家》就是其中的代表,本书以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和政治组织为研究对象,“印度化”这一概念也显示了赛岱斯的立论——事实上,这是二战前东南亚地区研究的重要特征。研究东南亚的大部分学者此前对印度和中国历史文化有所涉猎,在研究过程中遭遇“本地文化受到印度或中国影响”的现象时,都会予以特别关注。从东南亚地区被称为“印度支那”,也可以看出西方学者的取向。<br>二战后,作为整体的东南亚研究走上正轨。1950年康奈尔大学设立东南亚项目,并带动了一批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出现,也出现了不少作品。《剑桥东南亚史》中就列举了查理斯•费希关于东南亚社会、经济和地理的著作《东南亚》、约翰•卡迪的著作《东南亚的历史发展》(1964年)和《战后东南亚史》(1974年)、尼古拉斯•塔林的著作《东南亚:过去和现在》(1966年)等。 而“东南亚”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学术著作中,是在1955年。英国学者霍尔博采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的东南亚历史相关研究的成果,完成了《东南亚史》。这本书被称为20世纪中叶最重要的东南亚史著作,也为东南亚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打下了基础,铺陈了一种可能性。这本书被翻译成各个版本,是全世界范围内东南亚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东南亚本地区学者的研究更是蓬勃发展。 <br>(二)华人与华侨 <br>本书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东南亚之影响为题,华人华侨作为传统文化传播的载体,其作用不可忽视。华人与华侨是一组常被混淆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前身,则可上溯到“唐人”。在“华人”的称谓出现之前,中国古人是以“唐人”的身份为世界所认知。<br>“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清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一书中曾指出:“谓唐人者,如荷兰、暹罗诸国。盖自唐始通中国,故相沿云尔”,可见荷兰对国人以“唐人”相称;而海外国人也常以“唐人”自居,“唐”凝聚了一个种族的共同情感,代表着共同的祖先和文化经验,是研究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华人不可回避的概念。中华民国成立后,“唐人”逐渐被“华人”这一称呼更替。其渊源可以上溯到“华夏族”,中华民国的建立,使得“华”又被赋予了新的色彩。<br>华人是指所有具有中国国籍或祖籍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前,海外华人和华侨,即侨居在海外的具有中国国籍的人,是同一概念。海外华人国籍成为“政治问题”始于晚清。<br>在本国子民远投海外这一问题上,中国政府一直持反对立场。1740年10月,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即雅加达)疯狂屠杀华侨,巴达维亚城内数万华人,仅生还一百五十余人,惨绝人寰,史称红溪惨案。此事传入国内,朝野震惊。然而清廷对此事却表现冷漠,认为这些海外华人“违旨不听招回,甘心久往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可见在此事上,海外华侨仍被视为“得而诛之”的天朝叛民,其国籍上不存在任何疑问,华侨保护也无从谈起。<br>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强行打开,清政府不得不松动立场。1860年与英国签订的《中英续增条约》第5款规定:“戊午年定约互换以后,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处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各口地方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中法续增条约》之中也有类似条款。此禁一开,契约劳工大规模出现。据统计,19世纪前50年,出国华工总计为28万人,而1850年—1875年25年间,这一数字陡然上升至132万人,两者相较,年增涨为8倍。<br>然而这些契约劳工出国之后的遭遇十分悲惨。他们主要被卖往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从事最为危险和艰苦的开矿、修路等高强度劳动,生活却极为困苦绝望,被称为“猪仔”。以古巴华工的遭遇为例,据统计从1847年到1874年陈兰彬赴古巴调查华工案,完成《古巴华工口供清册》的27年时间里,有12万多名华工来到古巴;而1880年到驻古巴总领事馆登记的华工仅为4万多人,余下8万多人,绝大多数在契约期未满就被折磨死了。陈兰彬有感于古巴华工的悲惨生活,留诗一首:“肉破皮穿日夜忙,并无餐饭到饥肠。剩将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海外华工生存状态沦落至此,相关案件层出不穷。<br>除上述所提及的契约劳工所面临的迫切需求之外,随着海禁的开放,旅居南洋的唐人与国内联系也日益加强,海外华人问题日益凸显。晚清政府此前所秉持的“按之大清律例,入户以籍为定,其变乱版籍者,有治罪专条”的消极态度,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外有列强压迫,内有洋务派求变,清政府不得不改变其不作为的立场,正视起对这一特定人群权利的保护问题。清政府的这一改变,明确地体现在《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1868年),即《蒲安臣条约》之中。《蒲安臣条约》在学界评价中,素来毁誉参半、众说纷纭。它为此后契约劳工大规模输出打开了大门,在客观上也实现了清政府签订该条约的本意———为与处理与列强之间由于华侨保护产生的问题提供了准则、树立了先例。<br>对海外华人提供保护,对保护对象的国籍界定是前提,《蒲安臣条约》第5条、第6条就专为国籍问题而设:<br>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两国人民自愿往来居住之外,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是以两国注定条例,除彼此自愿往来外,如有美国及中国人将中国人勉强带往美国,或运于别国,若中国及美国人勉强将美国人带往中国,或运于别国,均照例治罪。<br>美国人民前往中国,或经历各处,或常行居住,中国总须按照最优之国所得经历、常住之利益,俾美国一体均沾;中国人民至美国,或经历各处,或常行居住,美国亦必按照相待最优之国所得经历与常住之利益,俾中国人一体均沾。惟美国人在中国者,不得因有此条,即特作为中国人民;中国人在美国者,亦不得因有此条,即特作为美国人民。<br>这两款条约确定了清政府处理海外华人问题的两条原则:其一,允许海外华人申请入外籍,不过必须基于申请自愿;其二,华人虽居海外,但清政府仍保留海外华人的侨权,海外华人依旧是“大清子民”。这两条原则也被写入其后的1909年《大清国籍条例》之中,该条例在第一章“固有籍”中肯定了晚清国籍以“属人主义为主,属地主义为辅”的原则,即:<br>第一条,凡左列人等不论是否生於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一)生而父为中国人者。(二)生於父死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三)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可考或无国籍者。<br>第二条,若父母均无可考或均无国籍而生於中国地方者亦属中国国籍。其生地并无可考而在中国地方发现之弃童同。<br>1912年《中华民国国籍法》、1929年《中华民国国籍法》也遵循了这一原则,并承认双重国籍。海外华人可以同时拥有侨居国和中华民国国籍,都是中国人,无所谓区别海外华人和华侨。这种情况到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种种因素,我国立法不再支持双重国籍,如果海外华人选择了加入别国国籍,则自动失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区分华侨与海外华人的概念,则成为法律的必然要求。从此,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被称为华侨;而海外华人则专指加入他国国籍只是祖籍为中国的人,即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人。<br>由于本书所涉及的年代止于1949年,因而所指海外华人、华侨仍为同一概念。<br>(三)影响 <br>从以国家这一形式出现在东方起,“天朝上国”就成为华夏之国的标签,成为贯穿整个东亚古代史的主旋律。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文化位居世界文化前列,其影响力对东南亚也形成了辐射。本书中所提“影响”,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br>第一,官方交往中的文化传播。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官方交往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与东南亚之间的朝贡关系,是我国古代对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三国时期蜀汉政权诸葛亮开发缅甸,孙吴政权朱应、泰康出访扶南,到明代郑和下西洋,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友好往来源远流长。在官方往来之间发生的文化交流,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生影响的重要表现形式。衣冠的颁赐,历法的适用,书籍的赠与,宣慰使的设立,乃至科举制度的开放,都是文化传播的组成部分。<br>第二,东南亚华人的移风易俗。华人移民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更早于官方交往的历史,历经早期的偶然性住蕃、高僧取经到访,朝代交替时避难海外以及大规模的华人下南洋,时至今日,华人已经成为东南亚诸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新加坡这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外,在其他东南亚国家,华人人口也在国家总人口数中占据一定比重。东南亚华人被视为少数民族,称为华族。这些移民到东南亚的华人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礼法文化——风俗、习惯和礼仪,甚至包括法律制度等“随身携带”传到东南亚,经过百年演变,成为东南亚社会风俗习惯的一部分。 <br><br>二、本书的基本构架<br><br>本书共分为导论和四章,以中国与东南亚交往史上的重要事件为切入点,介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整理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生影响的重要人物与群体,评述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深入东南亚的重要事件,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如何从一种异质文化最终演变成东南亚风俗习惯、东南亚国家法律文化的一部分。<br>导论对书中所涉及的一些概念进行定义和解读,并对本书的逻辑结构进行介绍。第一章“中国与东南亚交流”,主要从官方往来和民间往来两个层面,对中国与东南亚古代史、近现代史上曾产生的交往进行介绍。以时间为序,在官方往来方面,主要列举中国与东南亚交流史上的“风流人物”和重要事件,评述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方面起到的作用;在民间往来方面,分别分析商人、僧侣、华工等群体前往南洋并定居的原因,对近代时期东南亚华人的生存状况以及人口总量进行数据分析。<br>第二、三章以明代中叶中国影响“退出”东南亚以及西方列强进入东南亚为分界线,分期对殖民前与殖民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东南亚的影响进行评述。在第二章“天朝秩序与东南亚——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前殖民时代东南亚的影响”中,首先对前殖民时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进行概述,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影响东南亚的诸种表征。然后围绕着“郑和下西洋”这一中国古代中外关系史和交通史上的最重大事件,列举透过这一壮举,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如何对东南亚产生影响,并对明朝前期中国影响力“支配”东南亚秩序的原因进行解析。在第三章“传统礼法与海外华人社会———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殖民地时期东南亚的影响”中,以华侨社会中最重要的五个要素即殖民政府的华侨管理机构、华侨三宝(华侨社团、华文教育与华文报纸)以及华人宗教为切入点,分析这些构架华侨社会的重要支柱中的中国元素,透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中的运行轨迹。<br>第四章“华人国家的法律文化:新加坡”,通过儒学在华人主体国家的新加坡中的流转,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新加坡政治体制以及法律文化的影响。<br>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