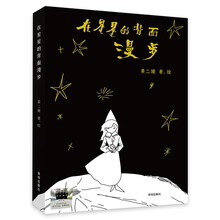“将计就计,听说过吧?一个资深的老贼从监狱里出来,洋洋得意地炫耀自己的遭遇:那些警察对我就是没办法呀!老虎凳,辣椒水——没用!老子坚贞不屈!于是,他们用上了美人计。老子将计就计,哈哈哈……然后表演了一番如何将计就计。旁边的一个小贼听了暗暗羡慕,于是自投罗网。老虎凳,辣椒水,这小子一声不吭。警察火了,一声大吼:拉出去毙了!这小贼急得大叫——喂,美人计还没用!”
可以预想的哄堂大笑。一个临时集体之中,擅长说笑话的人多半会自然地成为核心人物。机智和幽默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江湖习气。
时代的确不同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充当精神领袖的人物必须用诗与哲学武装到牙齿,搬弄起各种深奥的“主义”如数家珍。这些人显然不愿意装扮成楚楚动人的奶油小生——额上的皱纹表明了深刻的内心,络腮胡子象征了男子气概,如果脸颊上有一条无伤大雅的疤痕可以赢得更高的崇拜指数。可是,如今这种偶像已经过时。一本正经地思考世界肯定有些傻,过剩的理论只能造就一副苦大仇深的神情。要在一堆陌生人之中打开局面,笑话绝对比酸文假醋的格言有效。笑一笑,十年少,何必劳心费神地与诗或者哲学苦苦搏斗?令人惊异的是,如今居然冒出了那么多能说会道、滑稽俏皮的人物。古人云,三人行必有吾师;今人云,三人行必有幽默大师。从表情、腔调、节奏到耍贫嘴的遣词造句,他们的逗笑本领无可挑剔。即使周围笑得前仰后合,他们仍然可以不动声色,故作痴呆。我猜想,许多人的幽默才能多半是由无数机智诙谐的手机短信训练出来的,就像许多人的歌唱才能来自卡拉0K的开发——我愿意相信,多年之后历史学家必定会提出一个可爱的结论:手机与卡拉0K无疑是影响中国文化史的两种伟大机器。至于某些电视台那些妙语连珠、满脸坏笑的主持人,每一个表情和每一个动作都会让人喷饭。由于他们的“欢乐总动员”,我们时刻生活在喜剧气氛之中——这时我们才发现,以往那些诗、哲学或者什么“主义”让我们活得多么压抑!
据说英国式的幽默具有较高的智慧含量。笑声出口之前,我们的脑子已经转了一圈。英国式的幽默多半含蓄、温婉,即使讽刺也不过电光石火般的一蜇。然而,如今我们皮厚了许多,我们的神经由于各种风沙的摔打而逐渐迟钝。这时,只有大酸大辣的表演才能抓住周围的眼睛,令人粲然一笑。这终于酿成了另一种喜剧风格。一个埋没风尘的喜剧演员突然脱颖而出——他擅长的种种无理取闹的逗乐伎俩终于有了一个合法的名称:“无厘头”。周星驰、“无厘头”与《大话西游》出其不意地风靡一时,众多年轻的模仿者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念念有词地背诵剧中人的对话。短暂的观望之后,正统的文化机构决定赶这个时髦。北京大学给予周星驰的隆重礼遇表明,他的风格得到了学院精英的首肯。周星驰不再是一个喜剧演员——而是一个文化偶像。粗糙?缺乏细腻的表情?用力过度?穷凶极恶地逼迫别人笑出声来?——这些指摘已经没有多少意义。那些学院精英可以调集一大批后现代理论术语证明: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劲!
尽管考证不出“搞笑”这个术语是由哪一位高人首倡,但是,我深知“搞”这个动词的分量。笑声不再是水到渠成,而是搔胳肢窝似的“搞”出来的。当年,我们多么佩服王朔的喜剧天分——他的小说之中竟然堆积了那么多俏皮话。我们坚决地相信,葛优这种演员是王朔训练出来的。如果没有王朔提供的台词,葛优的冷幽默恐怕只能年复一年地封存在冰箱里面。现在,我们逐渐意识到一个可喜的事实:喜剧天才远比预料的多。那么多“戏说”的电视剧轻松地把血腥的历史调成了斗嘴的文字游戏,《家有儿女》逗得举国上下合不拢嘴,几个以“恶搞”为乐事的家伙竟然把著名导演折磨得捶胸顿足。文人相聚的一个饭局上,我亲眼目睹一个含情脉脉的故事如何被改写为“无厘头”的笑料。一个流浪文人看上了杭州西湖边茶楼里的一个端茶的女孩儿,接下来的故事该怎么办?众多文人一拥而上,分工合作,群策群力。从爱情的表白、遭拒、痛苦不堪到计谋、转机、赢得芳心,每一个段落都得到了“无厘头”式的加工。加工者个个才华横溢,工艺纯熟,以至于最初提供这个故事的作家不得不将深情的眼神改换成玩世不恭的嬉笑。我们身边“无厘头”式的爆笑如此之多,相形之下,相声反而成为一个毫无想象力的乏味节目。
“无厘头”式的狂欢生机勃勃,百无禁忌,甚至大举入侵某些与喜剧无缘的传统领域——例如警察或者侦探的故事。成龙或许算得上始作俑者。警察与凶手的对抗通常以命相搏,惊险万状;然而,成龙竟然在间不容发的打斗之中插入各种小噱头,令人忍俊不禁。我们似乎厌烦了将英雄想象为钢筋铁骨的硬汉。威风凛凛,君临天下——此外,他们是不是也有各种狼狈相,也会给我们提供各种笑料?随后,武侠故事闻风而动。《武林外传》的诞生表明,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侠已经被“无厘头”缴械。传统意义上的武功盖世或者侠肝义胆沉没在嬉皮笑脸的油腔滑调之中。
在我看来,“无厘头”最为杰出的胜利是征服了爱情领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男子汉气概是打动芳心的重要筹码。从007、硬汉小说到沉默不语的高仓健,这些重量级的男人始终是爱情领域的风向标。许多知识女性对于弱不禁风的奶油男生相当鄙夷,公然提倡“寻找男子汉”。这个口号的效果是,一批自认为有望入选的男子汉急急忙忙地给自己贴上胸毛。然而,“无厘头”不屑地将所谓的男子汉撇到了一边。《鹿鼎记》之中韦小宝实践的似乎是另一条民间的真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个无赖的投机小人竟然在爱情领域频繁得手,一大串女人围绕在他的周围争风吃醋,这充分证明了爱情气氛的改变:这种瘪三式的形象走红的时候到了。“无厘头”如何成功地将传统的男子汉形象挤出爱情领域?韦小宝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码。
坦率地说,我对于“无厘头”没有多少好感——笑不出来。我有时会奇怪地询问几个学生:为什么周星驰的一个鬼脸就可以让你们开心地笑这么久?他们暧昧地相视一笑,没有回答——我知道他们想说的是,这个家伙已经老了。为了表示对于周星驰并不陌生,我多少违心地做一些妥协:我承认,《功夫》这部电影的上半部分还是有点意思。几个学生这回忍不住了:啊呀老师,我们不断地重看这部电影,就是等着看下半部分呢!
无论周星驰多么有号召力,我从未担心“无厘头”如同瘟疫似的蔓延。“无厘头”不可能侵入医学领域,谁会让一个医生疯疯癫癫地诊断病人?“无厘头”也不可能侵入金融业。如果一个装神弄鬼的会计扣下了一半工资,最虔诚的“无厘头”崇拜者也饶不了他。即使夫妻之间分派谁洗碗,谁打扫房间,“无厘头”也解决不了问题——几句着三不着两的俏皮话改变不了固定的家庭分工。我想说的是,我对于“无厘头”的厌弃来自一个重大的怀疑:我们的生活值得享用这么多笑声吗?
一个电视记者曾经倒扛着摄像机在街上走了一天。整理街头随机拍摄的种种影像时,这个记者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他所拍摄的全部面容竟然没有一张笑脸。某种程度上,这个事实可以从另一处找到诠释:一位教师在课堂上出示了一幅图画,画面上一对夫妇在午后的灿烂阳光里酣睡——教师出了个题目“突然”,让学生自由想象后续的情节。这位教师同样震惊的是,交上来的所有作业均是虚构各种灾难的突然降临,无论是财物被窃、几个流氓的突袭还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大雷雨。这么一种集体的悲剧感从何而来?如果这种悲剧感时刻蛰伏在内心的暗处,“无厘头”提供的哈哈大笑犹如没心没肺的傻乐——“梦里不知身是客”。一个年轻人参加汶川大地震的救援行动后返回故乡,突然感到了微笑的可耻。如此惨痛的经验之后,笑成了一种令人恶心的行为——我相信这种感觉。
当然,不管是不是喜欢“无厘头”,我们都没有理由否认作者们的奇特想象——妈的,这真是一批聪明人呵。可是,我们的内心同时清楚,没有人会真正地将自己的生活托付给这些聪明人,尽管我们会被他们的喜剧天才逗得哈哈大笑。P6-9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