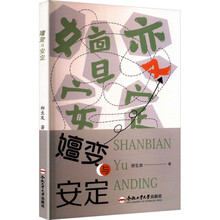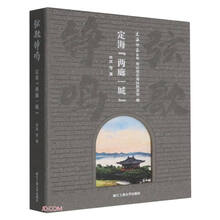《翦拂集》选
祝土匪
莽原社诸朋友来要稿,论理莽原社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当代名流,当然有与我合作之可能,所以也就慨然允了他们。写几字凑数,补白。
然而又实在没有工夫,文士们(假如我们也可冒充文士)欠稿债,就同穷教员欠房租一样,期一到就焦急。所以没工夫也得挤,所要者挤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是挪用、借光、贩卖的货物,便不至于成文妖。
于短短的时间,要做长长的文章,在文思迟滞的我是不行的。无已,姑就我要说的话有条理的或无条理的说出来。
近来我对于言论界的职任及性质渐渐清楚。也许我一时所见是错误的,然而我实在还未老,不必装起老成的架子,将来升官或人研究系时再来更正我的主张不迟。
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这也是祝《莽原》恭维《莽原》的话,因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主稿诸位先生当然很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至少总不愿意以“绅士”“学者”自居,因为学者所记得的是他的脸孔,而我们似乎没有时间顾到这一层。
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金牙齿没掉么?雪花膏未涂污乎?至于骨头折断与否,似在其次。
学者只知道尊严,因为要尊严,所以有时骨头不能不折断,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日,我固完肤也,呜呼学者!呜呼所谓学者!
因为真理有时要与学者的脸孔冲突,不敢为真理而忘记其脸孔者则终必为脸孔而忘记真理,于是乎学者之骨头折断矣。骨头既断,无以自立,于是“架子”,木脚,木腿来了。就是一副银腿银脚也要觉得讨厌,何况还是木头做的呢?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极好的话,论真理与上帝孰重。他说以上帝为重于真理者,继必以教会为重于上帝,其结果必以其特别教门为重于教会,而终必以自身为重于其特别教门。
就是学者斤斤于其所谓学者态度,所以失其所谓学者,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
学者虽讲道德、士风,而每每说到自己脸孔上去;所以道德、士风将来也非由土匪来讲不可。
一人不敢说我们要说的话,不敢维持我们良心上要维持的主张,这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那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自己无贯彻强毅主张,倚门卖笑,双方讨好,不必说真理招呼不来,真理有知,亦早已因一见学者脸孔而退避三舍矣。
惟有土匪,既没有脸孔可讲,所以比较可以少作揖让,少对大人物叩头。他们既没有金牙齿,又没有假胡须,所以自三层楼上滚下来,比较少顾虑,完肤或者未必完肤,但是骨头可以不折,而且手足嘴脸,就使受伤,好起来时,还是真皮真肉。
真理是妒忌的女神,归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独身主义,学者却家里还有许多老婆,姨太太,上坑老妈,通房丫头。然而真理并非靠学者供养的,虽然是妒忌,却不肯说话,所以学者所真怕的还是家里老婆,不是真理。
惟其有许多戛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孔的,并且也不想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
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来大思想家都被当代学者称为“土匪”“傻子”过。并且他们的仇敌也都是当代的学者、绅士、君子、士大夫……自有史以来,学者、绅士、君子、士大夫都是中和稳健,他们的家里老婆不一,但是他们的一副面团团的尊容,则无论古今中外东西南北皆同。
然而土匪有时也想做学者,等到当代学者夭灭殇亡之时。到那时候,却要请真理出来登极。但是我们没有这种狂想,这个时候还远着呢。我们生于草莽,死于草莽,遥遥在野外莽原,为真理喝彩,祝真理万岁,于愿足矣。
只不要投降!
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 ——纪念孙中山先生
记得一二月前报上载有一篇孙中山先生的谈话,他说:“我现在病了,但是我性太急,就使不病,恐怕于善后会议,也不能有多大补助。”我觉得这话最能表现孙先生的性格,并且表现其与普通中国人性癖的不同。因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且孙先生之与众不同正在这“性”字上面,故使我感觉改造中国之万分困难。如鲁迅先生所云,今日救国在于一条迂谬渺茫的途径,即“思想革命”,此语诚是;然愚意以为今日救国与其说在“思想革命”,何如说在“性之改造”。这当然是比“思想革命”更难办到,更其迂谬而渺茫的途径。中国人今日之病固在思想,而尤在性癖,革一人之思想比较尚容易,欲使一惰性慢性之人变为急性则殊不易。中国今日岂何尝无思想,无主义,特此所谓主义,纸上之主义,此所谓思想,亦纸上之思想而已,求一为思想、主义而性急,为高尚理想而狂热而丧心病狂之人,求一轰轰烈烈非贯彻其主义不可,视其主义犹视其自身革命之人则不可得,有之则孙中山先生而已。难怪孙中山有“行之匪艰知之维艰”之学说。
若由历史上求去。性急者每每为中国人所虐待,乃至显的事实。中国也本来不喜欢性急,故子路早已得孔子“不得其死然”的诅咒。若屈原,若贾谊便略可为中国性急者之代表,尤其是贾谊,然贾谊也早有苏东坡之诌其短见。此乃中庸哲学及乐天知命道理之天然结果。徐先生的非中庸论诚是:“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猛进》第三期答鲁迅语)个人以为中庸哲学即中国人惰性之结晶,中庸即无主义之别名,所谓乐天知命亦无异不愿奋斗之通称。中国最讲求的是“立身安命”的道理,诚以命不肯安,则身无以立,惟身既立,即平素所抱主义已抛弃于九霄之外矣。中国人之惰性既得此中庸哲学之美名为掩护,遂使有一二急性之人亦步步为所吸收融化(可谓之中庸化)而中国中稍有急性之人乃绝不易得。及全国既被了中庸化而今日国中衰颓不振之现象成矣。即以留学生而论,其初回国时大都皆带一点洋鬼子之急躁性,以是洋气洋癖,时露头面,亦不免为同事者所觑笑,视为不识时务。由是乎时久日渐少有不变为识时务及见世面之时贤。及其时务已识,世面已见,中庸不偏之工夫练到,乐天知命之学理精通,而官运亨通名流之资格成矣。
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性格不大象中国人,是指孙中山先生不像现代的中国人。至于孙中山先生能不能像将来的中国人,这便是吾人今日教育之最大问题。果使孙中山是像将来的中国人,那末我们也可不必为将来的中国担忧了。要使孙中山先生像将来的中国人,换言之,要使现代惰性充盈的中国人变成有点急性的中国人是看我们能不能现代激成一个超乎“思想革命”而上的“精神复兴”运动。
岂明先生已经说过:“照现在这样做下去,不但民国不会实现,连中华也颇危险……‘心所为危不敢不告’,希望大家注意。”(《语丝》第十九期)诚然应希望大家注意。
提倡“精神复兴”我觉得是今日言论界最重要的工作。
回京杂感
岂明先生来信谓:这回南下一定得到许多见闻,希望能写出来。我想这三个月之间在南边固然有些事件,但是何尝有北京所闻所见之足以引起我们的感叹?据报上所载种种奇闻,如阴谋复辟,“整顿学风”,还有种种名流之怪论,与我在厦门所闻见张毅吃人一类的消息相比,何尝稍让丝毫——老实说起来,还要光怪离奇些!这似乎就是岂明先生所谓“有些当出于老兄意表之外的”及玄同先生所谓“成日在苦闷无聊的状况中一面看了种种(广义的)遗老遗少遗小遗幼们之精神的复辟……颇觉有‘气炸了肺’之象”。记得我走之时正是某某名流大说鬼话之秋,(虽然此位名流也曾“大打玄学鬼”,回想至今只差了两年,可叹!)今日回来又正是某某名流大唱“政治修明,实业发达,军备充实,教育进步”(虽段祺瑞的大执政令也不过尔尔),而学生“爱国心”倒可以不要,至少也应该诋毁之际,呜呼玄同,我们虽欲不“气炸了肺”其可得欤?且岂独“气炸了肺”而已,我们简直非效喇嘛开打鬼大会不可。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