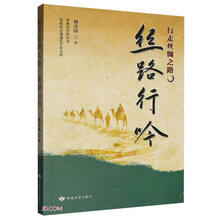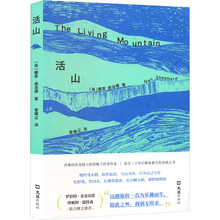真正的春寒料峭,她的桃红色风衣穿得也未免早了些,就连最性急的桃花还没有开呢。
她内心本来是很急切的。今天_2001年春运刚刚结束的日子,对她来说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转折时刻,她结束干腻了的旅行社的工作,即将担任美金证券公司的部门经理。对于玩股票这个行当,她历来兴趣是很浓的。上高中那阵子还爱好过一段文学,看过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对于当时上海交易所那套玩意儿觉得很有一种神秘感,前几年还随着自家老公炒过几笔小小的股票。也怪喽,凡是老公经手买进的,至多是不赔不赚打个平手;而只要自己一插手,或多或少都能发个小财。后来,因为旅行社领导比较器重,业务又忙,暂时在炒股那方面收心了。可今天,不是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股民前来看风色押宝,而是作为主家来玩大户,这倒是个很有挑战性的行当。她从小就喜欢拨弄脑瓜里的转轴,这回且真要大试一把哩。
心里急切自管急,还是得绷着性儿晚点赴约,但也得把握住度,以不引起对方太大反感为宜。一看小坤表,十四时十五分,正好,出门“打的”,一刻钟准到。习惯的“打的”姿势,左手五根小却并不柔嫩的手指自然地撒开,手臂略微下垂,以达到示意目的就行;切忌大幅度摆动,而且不可过分上扬,那样还够不上一个标准的白领阶层。
“小姐去哪儿?”
“二十一世纪饭店。”
在饭店一层右手大厅。透过眼镜片,看得见那人正坐在北面临窗的大沙发上,右手分明在茶几上弹着,显然是等得焦急了。不过呢,没事儿,他还走不了。
那人见她来了,有点故作深沉,指着对面的沙发请她落座。
“黄总,抱歉,叫您久等了。我其实出来得并不晚,建水桥这边堵车堵得厉害。咳,没办法。”
“嗯。”黄总脸上的愠色一掠而过,随即是做出来的宽松。“其实,我来得也不算太早。”他的神态和个头都有点像当年让华夏多少女孩儿亏了不少觉、黑了眼圈的那个风靡电影界的东瀛男人高仓健,只是言谈举止比高仓健粗糙得多,当然这也是仅就银幕上的形象而言。
“不管怎么,多谢您黄总了,要不是您的大力帮助,当然,也是多亏了您的老战友在美金公司掌权。但要是没有您从中搭桥,再合适的事儿也成不了。”赵世鸿说着,从自己的坤包里拿出一大一小两个小红盒。“黄总,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实在不成敬意。这是本世纪开始发行的金币两枚,也算是我们共事几年的纪念吧。这一个是文革中一家金矿做的纯金的毛主席纪念章。我知道您喜欢收藏,也算名物有主吧。”
还真是,黄总对那两枚金币倒并不十分眼亮,可当他一打开那个方寸小盒,看到着军装的毛主席像下面有一标签,上有4.5克字样时,顿时喜不自禁,话锋又直又粗:“小赵,你算是看到我心坎上了,我就是有这么个收藏的爱好,尤其是这类东西,真金的,没错,好!好!”
他将两个小盒都装进自己的黑皮包里,一见对方那件桃红色的风衣还穿在身上,便打个手势:“把外衣脱下来,多热啊。”
“不热,这厅里温度不高,再说我过一会儿就要……”她的小巧的身子动了一动,复又坐定了。
“那也好……”黄总对她刚才做出的反应显然并不如意。三年了,她就像狡兔,不,又似警犬那样警戒着他,而且一次再次地闪过了他的追索和诱捕。眼前这个环节是关键的关键,他这一宝押得很沉,心里也很疼,使出浑身解数帮她如愿以偿地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此恩非小,仅仅仨瓜俩枣就打发了?太冤了!他极想拿下这个身材不高的制高点,也算了却了三年的夙愿,以免造成无法弥补的缺憾!
黄总正思虑间,对面小赵的手机响了。只见她厌烦地一皱眉头:“哦,是二姐,怎么?心脏病又犯了?哪儿?哦,北海医院,嗯,那儿水平还行。怎么,现在就过去?不成,我手头上的事太忙,实在走不开!嗯,明儿看情况吧,我尽量!”她显然不等对方还口,果断地关上了手机。
“病了?”黄总本能地问了一句。
“我爸。老病了,真烦人!”她情不自禁地喷了一句。每在最烦心的时候,她那鼻翅儿总是像青蛙眼似的一鼓一鼓的,但并不难看,反而有一种睥睨一切的威严。“在我的事业的关节眼上,怎么能分身呢?黄总您说是不?”
“是,极是!”他难得地蹦出一个古雅的字眼儿。心中窃喜:他判断她有点“黏”,连她父亲犯病人院都放弃了,说不定今天下午将有一个新的突破。他又作了一次试探:“小赵,我以前始终认为你是有背景的名门大家出身,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好的气质,后来……”
“后来才晓得我原来是出身小市民。”她惊人的伶牙俐齿,而且经常采取主动进击的方式;同时她的眉头狠皱了一下,说明内心已十二分的不耐烦。真的,她的眉毛又黑又粗,与那张小型的香瓜脸略显不大相称。在平时心性平和时还不大显,但在忒不耐烦时,眉毛就像长了一倍。对方显然曾经领教过这种变异,一时有些尴尬地捻着被烟蒂熏黄了的手指头。
“无聊!”她在心里啐道。这样的话,他不知说过多少回了。而她从来不装饰自己,说:“我嘛,父亲年轻时蹬过三轮,后来在旅馆里管过杂务;母亲年轻时在饭店里端过盘子,后来连生了几个孩子,退职回家,在街道上干过几年业余侦缉队,不过,她可不是小脚的。我嘛,全家唯一的大学生,毕业于名牌大学外语系,英、法、日三种外语,不算精,比二把刀强点儿!”
这番话,从几年前面试时她就对面前这位黄总说过,难道他就像忘了似的,今儿个又老话重提,什么“我开始总以为你是名门望族,大家出身哪”,一个一米八的大汉,这么啰里啰唆,烦不烦呀!她想到这里,斜觑着一看表,都快四点了。行啦,看在他帮了大忙的情分上,整整陪聊了一个多钟头,够对得起他的了。约定今天四点半去美金证券公司与张总见面,她决定就在今天办完一切手续。这样,从今天起就完全成了“美金”的人,与华球旅游公司彻底脱离了关系。什么事都是一次性的:过去是,今天也是——这一个钟头本身就是一次性的,缘分到此为止。
当然,这都是世鸿女士的“内部语言”,黄总贾龙先生是透视不出来的。他仍然抱有一线希望:计划在对话至黄昏时刻,再到附近目前最火的西餐馆“多瑙河之波”撮上一顿,然后,事态或许会有中等程度的进展……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对面的她站了起来:“对不起黄总,那边的张总约我过去交代工作,真是身不由己。好在你们俩是过去的老战友,彼此都是理解的;又好在,我到那边离华球也是很近的,我们难免工作上还有些联系,后会有期吧。”
“怎么?”久经阵势的黄贾龙先生一时也有些愣怔。他最能破译她这类“后会有期”等词语内涵是什么: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不止一次领教过这种使他难堪而后又心存希冀的招数。
“明天再去那里不行吗?”
“那恐怕不行。”她笑得似乎有些齿冷,“张总那边毕竟是初识,咱们总是彼此了解的老同事了,我想您是最理解和支持我的革命行动的。”她最后还来了一句小小的调侃,又伴以一个令人齿冷的微笑。
“好吧。”他无奈地一搓手,像一个男子汉那样站起来,“小赵,你怎么走?我送送你。”
“不好意思,我知道黄总您忙,就不要送了吧。”
“难道送一送还多余吗?”
“哦,这说哪去了,不多余,不多余。”三十五岁的她表现得进退自如,超常地老到。
出了“二十一世纪饭店”大门,门口就是地铁站,她说她要乘地铁去那里。黄贾龙尽管并不坐地铁,还是决定送她上车。在下一溜台阶又上另一溜台阶时,并排走的他试探地用左手揽着她的腰身。她敏感地向外一闪,不冷不热地甩了句:“我自己会走。”
他的手,像老化的牛皮筋似的无可奈何地缩了回来。这时刻,他的双脚仿佛与大脑脱离了关系,只是机械地抬着步子;但他的大脑仍然保持着独立的运转,至少在眼前这个作战对象上,他是完全失望了。一时间,他后悔帮她实现了工作的转换:“看来是羊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