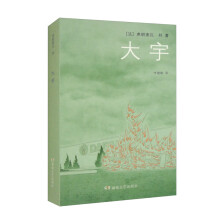鼓舞——纪念范泉先生
陈映真[台北]
重新发现范泉(一九一六——二○○○),是这世纪之交海峡两岸文学界十分重大的收获,也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
早在艰苦的抗日战争的晚期,年轻的范泉就在孤岛上海苦心收集了有关台湾文艺的日文资料,一面在敌伪的虎视下对侵略者进行果敢的文化斗争,一面又满怀着对同胞亲人的情感,研究祖国失丧之地台湾的文学。一九四六年元月到一九四七年间,范泉在大陆的文化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台湾文学的重要文章。今日回顾,范泉是当代中国大陆最早,而且很有见地的从事台湾新文学研究的人,是今日大陆自一九七九年后不断繁荣起来的台湾文学研究事业的肇基人。
更重要的是,范泉有关台湾文学的研究在甫告光复的台湾文坛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起到深刻的影响。一九四六年元月,范泉在上海发表《论台湾文学》。二月,台湾重要的文学理论家赖明弘投稿到上海同一个杂志(《新文学》)上作了热情的回应,支持范泉的这些意见,即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台湾光复后,台湾文学进入了将自己建设为新中国、新社会之组成部分的台湾文学的时代。
一年多以后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仅仅与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惨案”相隔七个多月后,欧阳明在台湾岛内的新生报《桥》副刊上发表文章《台湾新文学的建设》,第一次在岛内回应了范泉,从此在台湾引发了一场为期一年许的关于“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争鸣。参加争鸣的省内省外作家和评论家有二十六个人,计收获了四十一篇论文。思想争鸣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围绕在范泉《论台湾文学》所提出的四个焦点上:(一)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一环;(二)台湾新文学发轫于日本统治时代,备受压抑,发展不足。光复后,台湾新文学迎来了一个重建的时期;(三)重建台湾新文学的目标,是要使台湾新文学与大陆新文学齐头并进;(四)但台湾新文学的重建工程,端赖本省本地作家的努力,才能建设有“台湾气派”、有“台湾代表性”、有“台湾风格”与“台湾个性”的台湾新文学。第二个部分,是把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理论及其运用介绍到台湾(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个性与典型性、文学的统一战线、台湾与大陆文学的特殊与一般的辩证法、继承还是超越“五四”,等等)。第三个部分则是当时台湾思想界面临的具体问题(如“台湾文学”的概念、关于“奴化教育”、关于“奴才文学”、关于省内知识分子、民众之间的团结,等等)。而在这论议的三大部分中,主要的论议则集中在范泉所提出的上述四个焦点上。从台湾文学思想史看,范泉《论台湾文学》引起的这场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讨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而且很有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在台独派的宣传下,造成这样的刻板认识,即认为台湾光复后,由于中国普通话和台湾的闽语、残留日语之间的隔阂,再加上国民党恶政的威暴,岛内的省外人士与本省人士之间、国内省外人士与本省人士之间无法沟通,心有芥蒂,甚至相互疏隔。范泉的台湾文学论在台湾引起重大思想、文化反响的事实,不但粉碎了这种政治歪曲,还进一步呈现出即便在“二·二八惨案”之后,祖国两岸人民之间在同一个历史形势下的热切互动。范泉在战后对台湾的重大思想影响,说明大陆的重要报章杂志流传于台湾,不少进步的大陆文化人来台,向大陆报道国民党治下台湾的各方面,并与台湾当地进步文化人互相团结,初步形成了两岸人民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在国共内战形势迅速转化的时局下,通过当时两岸间的“公共领域”,凝结了一种政治的、文化的、文学以及思想的共同体意识。而正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的共同体意识,使两岸先进的知识分子能够超越国民党的屠杀、镇压与恶政,坚定地寻求民族的和平与团结,共同面向中国之新的未来。而历史显然选择了范泉,让他在那历史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启蒙与促进的作用。
在台湾文学的研究上,范泉能够很敏锐地理解台湾文学作品中的审美要素——例如他以“丰厚的光彩”来形容杨逵的作品,以“静谧和忧悒”概括龙瑛宗的作品,并从而以杨云萍为“兼备杨逵的丰厚与龙瑛宗的宁静”,颇能把握作品审美的神髓。另一方面,范泉也具备深刻的政治理解力。他说杨逵“不曾被任何人所御用”,“从没有为(日本)军阀侵略政策宣传”过,坚持到底,有“很骄傲地直立着”的高大形象。寥寥数语,却极其准确地概括了杨逵的文学道德与文学人格。当他说到台湾附日作家周金波时,说“周金波写下了屈辱求荣的《志愿兵》一类的小说而仍然毫不感到自惭”。去年去世的周金波确实是至死不悔其附日作品,至死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此外,范泉在《记台湾的愤怒》这篇同情和声援经受“二·二八惨案”残暴镇压的台湾人民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台湾从异族的铁蹄下重又归返祖国的怀抱。对于这样一块有历史意味和民族意识的土地,我们应当用怎样的热忱去处理呢?是不是我们要用统治殖民地的手法去统治台湾?是不是我们可以不顾台湾同胞的仇恨和憎恨,而拱手再把台湾送到第二个异族统治者的手里呢?
今天台湾民族分离运动的兴起有多端。其中国民党对台“殖民地手法”的统治是原因之一。范泉五十三年前的这一段话,在关于正确处理对台工作、面对台湾问题上,至今仍充满了深刻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说明范泉的台湾研究带有清醒而深刻的政治认识力。
其次,在“二·二八惨案”后不久,范泉写《记台湾的愤怒》,表达了他对恶政下的台湾同胞的深切关怀与同情。杨逵在“二·二八惨案”中失踪的消息讹传到范泉的耳朵,他写了充满情感和理解力的《记杨逵》,深情地挂念从未谋面的杨逵。“现在,虽‘二·二八’事件已经有半年之久,询问了许多台湾的朋友,杨逵的消息却依旧是杳然无闻。”范泉写道:“我每次用颤抖的手,翻阅着他亲笔签字赠送给我的遗著,一阵难堪的感受涌上了我的心头……”范泉为杨逵忧烦焦虑的真情,今日读之,依旧令人动容。
去年(一九九九)十一月,范泉由于台湾几个研究历史的朋友错误的查证,将曾在《文艺春秋》刊出优秀小说《沉醉》的、在台省外作家欧坦生,误为在一九五。年代台湾肃共恐怖中殒命的蓝明谷。事隔五十多年,初听误信蓝明谷即欧坦生已遭国民党杀害,时已罹患末期癌症的范泉悲痛不已。在他生命最终的时日,范泉强忍病痛,以颤抖僵直的手,写了三千六百余字的他一生中最后的文章:《哭台湾作家蓝明谷》。“我听到这一噩耗,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哭了!”他写道:“我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我哭了!”
据范泉夫人吴峤女士说,范泉平生只流过三次眼泪,一次是流放中闻母丧;一次是知自己重病行将与爱妻死别;第三次是听说蓝明谷的死讯。这说明范泉研究台湾和台湾文学,绝不只把研究当成漠然的职业与日课,而是投注了同胞、亲人似的深切真挚的感情的。
对台工作和台湾研究,应该持清醒深刻的政治认识力,也应该对研究的客体——台湾、台湾人民和台湾文学,怀抱一份同胞、亲人似的真挚深沉的感情。
这就是台湾研究的先觉者和肇基者范泉留给今日吾辈的一个发人深省的启示。
一九九九年秋中,范泉来信,希望在台湾我的小出版社出版他抱重病自选、自编的散文集《遥念台湾》。十一月廿七日,他编好书稿,写了一封信给我。在信末,他这样写:
我可能不会见到这本书的出版了。出书以后,请寄给我老伴吴峤几本,以便分寄几个儿女,别的没有什么要求。
非常遗恨,我们刚通信认识,可能就要永别了……
我记得读完来信,已是满面泪痕,我快马加鞭地赶,但毕竟没有赶得上让他生前看见这本书在他早已“遥念”的、祖国的岛屿台湾出版,更没有来得及和敬爱的范泉先生见上最后一面,至今思之,犹有馀痛。
经历反右和十年“文革”极左风暴的摧残,范泉流落到遥远的青海,经受了不可置信的折磨。一九七九年他获得解放,但还是等到一九八六年范泉七十岁才调回上海。
经历了这些在台湾的我所不能理解的苦难和坎坷,回到上海的范泉,立刻投入他被剥夺了几十年的文化工作。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