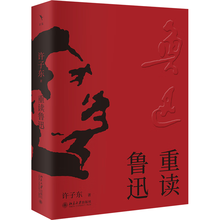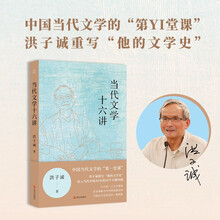这番话的遣词造句、语调情绪,都与作为严谨学者的钱理群一贯的风格不合。“生亦何欢,死亦何忧,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几句话实在平淡无奇。类似意思的话,可说不知有多少,因这几句话而“有一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实在不像是出自钱理群先生之口。钱理群先生乃饱学之士,尤其对鲁迅有精深的研究和理解。如果钱理群先生在“极度的精神苦闷”中对鲁迅的某句话、某篇作品有了新的理解、与鲁迅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鸣,那会更合情合理。毕竟,把钱理群和他的学生以及“把你,把我,把他,把我们大家的心灵沟通了,震撼了”的,更应该是鲁迅作品,而不是金庸那些远离尘世、虚无缥缈的武侠小说。钱理群的这番话,如果不包含着“讨论会”上特有的客气,那就只能说他是在叙说非正常状态下阅读金庸的体验。如果说,是在“陷入了极度的精神苦闷之中,几乎什么事不能做,也不想做,一般的书也读不进去”的时候,钱理群先生读起了金庸并且对其中几句原本寻常的话大为动情,那在正常的精神状态中,在其他的书能够读进去时,钱理群先生或许会对金庸的感受大不相同。不过,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金庸的书是在别的书都读不进去时独能读进去的书,而这样的书,肯定不是“正常”的书。<br>至于严家炎先生指出的“金庸热”的第四个特点,就更有些可笑了。转述或伤其真,也原文照抄:<br>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金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的看法却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他在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了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这样一种完全超越了政治分歧的阅读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br>读这段话,我首先还是惊异于严家炎先生对邓小平、蒋经国也读过金庸之事如此清楚。看来,严先生确实是花过一番工夫对金庸小说的被阅读情况进行调查的,平时也一定很留心搜集有关资料,尤其是“金庸雅迷”的资料。如果是在从事文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这种工作当然也可以做。但严家炎先生搜集这种资料的目的,却是为了证明金庸小说的价值。这种心态就很有点耐人寻味了。还是前面说过的话,如果严家炎先生十分确信金庸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那只须努力去发掘、去阐释这种价值即可,用不着又是统计金庸小说的读者量,又是抬出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来作旁证,用徐岱先生指责非议金庸者的话说,就是用不着“拉大旗作虎皮”。而严家炎先生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寻找旁证,是否意味着内心对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并无确信,是否意味着也时时对自己投身金庸研究怀有疑虑?若心态果真如此,却又硬挺着充当“金迷”阵营的排头兵,个中原因,又是什么?<br>再说,将“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的阅读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准,认为“完全超越了政治分歧的阅读现象”就“很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也真是闻所未闻。如果不同政治信念的人都喜爱吃臭豆腐,就能证明臭豆腐是味最美最有营养的食物吗?如果不同政治思想的人都迷恋于海洛因,就能证明海洛因是上好的东西吗?因政治信念的对立而对文学作品做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只在特定时期发生在特定作家作品身上,这本来就是一种非常态的现象,而对文学作品的评价“超越了政治分歧”,本是一种正常现象。可严家炎先生似乎在以非正常为正常,而将正常现象却视作特别值得思考和研究的特例了。这可说又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把蒋经国拉来为金庸助阵,也匪夷所思。在某些方面,我们不妨认为蒋经国乃行家里手,但在对文学作品的鉴赏上,却没有理由认为他也有高于常人的水准。蒋经国洁净的床头放着一本洁净的金庸,与大陆民工肮脏的床头放着一本肮脏的金庸,性质完全相同。这道理,前面在谈到著名科学家时已说过。以著名政治家也阅读金庸从而证明金庸有了不得的价值,还是犯了常识性错误。何满子先生说,这里奉行的逻辑是:“赵太爷田都有三百亩哩,他老人家的话还会错么?”是真正的“拉大旗作虎皮”。①话虽有些尖刻,但应该说是击中了要害的。严家炎先生新近作文反驳何满子先生,呼吁以“平常心”看待金庸。②而我觉得,恰恰是严家炎、徐岱等几位先生,未能以平常心看待金庸。例如,严家炎先生在推崇金庸时,一再犯常识性错误,恰恰说明心态的不平常。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