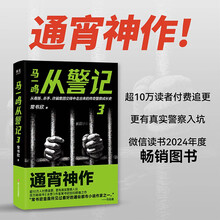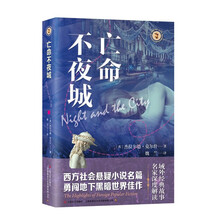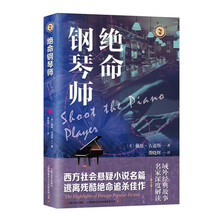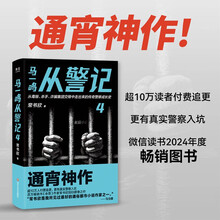第一章 天降飞贼
一
坐落在莫斯科西南部的伊凡大帝钟楼,高大突兀直指云端。这样的一个建筑不能不让人生出一些想象来:那里面一定藏着一些什么。
外国人的教堂里是从来不缺乏宝物的。莫斯科人就传说,属于全俄罗斯教会最值钱的宝物,全藏在钟楼最上面的两层。别的都不说了,单在夜晚,你抬头往上看,会有彩色的光晕从里面发出,那是宝石和夜明珠的光芒。真正宝石和夜明珠的光芒,箱子和柜子是锁不住的。
藏宝当然要藏起来的,如果明晃晃无人不知地摆着,那不是在考验莫斯科小偷们的忍耐力吗?小偷并不会因为财宝是教堂的,就不去偷。
但是,当你走近伊凡大帝钟楼,走近了看一看,就会明白无论怎样本领高强的江洋大盗也休想爬上伊凡大帝钟楼,除非你会飞。不过光飞还不够,还得变成一只猫:那几乎高入云端的窄窄的条状的窗口,人是钻不过去的。猫能。但猫们不爱财宝。
更何况,院子里还有两条比豹子还要大还要强壮的恶犬苗米和苗姆,天一黑就把它们放出来。而它们的机敏、聪明和责任感又给人以确信:哪怕你是神仙,也别想无声无息地接近钟楼。苗米和苗姆是由法国斗牛犬与西伯利亚牧羊犬杂交而成,凶猛异常是不用说,并且蔑视传统与规则:它们不叫,扑向敌人时不发出一声信号。有一次,一个不知深浅的小贼从围栏上翻了进来,苗米和苗姆只一口,两条胳膊,咔嚓一下,就给咬断了。断了的意思是连骨头都碎了。
伊凡大帝钟楼,最显著的特点是它82米的高度。在全市大大小小三百多座和全国三千多座教堂中,再没有哪一座可以望其项背。沿着它内部狭窄的旋转式的小楼梯爬上钟楼的顶层,会给你一种突然的豁然开朗:俯瞰全莫斯科城,周边30俄里以内尽收眼底。由此足可推测,古人建造它的时候,一定把战备的因素也考虑了进去。它绝对可以堪称全世界最高的烽火楼。
仅有高度是不够的,伊凡大帝钟楼的出名还有它那无与伦比的坚固性。拿破仑军队大炮的平射和希特勒飞机自上而下的轰炸,都没有撼动它。它高高屹立的样子就像个倔强的老人。从1543年建成以来它奇迹般地躲过了种种劫难,历时5个多世纪,直到今天它还那样令人叹服地屹立着。
有一种说法,伊凡大帝钟楼之所以能躲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而不毁,全是耶稣基督的保佑。这说法显然有失偏颇,因为公正的上帝不可能厚此薄彼地只“保佑”钟楼而不保佑那些曾被炮弹炸得粉身碎骨的教堂。实际上,剔除那些幸运的成分以外,钟楼设计合理、结构坚实,那看似笨重无比的花岗岩石精密的组合,才是它能屹立至今的关键所在。
1812年,拿破仑攻下莫斯科后,忽一日,他手下一队士兵憋得发腻,便决定拿钟楼上的大钟来取乐。
大钟不在钟楼的顶层,而在第四层与圣约翰教堂连接的部位。
伊凡大帝钟楼由两部分组成:钟楼与教堂。
伊凡大帝钟楼上的钟,也能占些全俄罗斯之最:最大和最多。钟楼上共吊着33座大钟,其中最大的一口名为圣母升天大钟,重4000普特。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乘以4000,想想吧,那该有多么重!俄国人一向以大为美,但很多人仍不明白造这么大个家伙有什么用,大得都有些傻了。这也难怪战场上也照样浪漫的法国人,要拿它寻开心:给它几炮,看能咋样。结果可想而知,大钟在一片或许悠扬悦耳的响声中化为一地碎片。
没关系,大钟毁了可以再造,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让人担心的是钟楼这座古老建筑。还好,拿破仑10公斤一个的炮弹落在它的身体上“嘣”一下就如弹个脑瓜崩。
伊凡大帝钟楼说白了就是个古城堡,它的防御体系固若金汤。萨布林大主教没有理由不安心睡觉。当然,睡着或睡不着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二
今夜,雨特别大,而且还伴随着一道道吓人的闪电。这与九月天气显得格外的不相称,也显得有一些怪异……
萨布林·维塞洛夫黑衣大主教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在中国的哈尔滨度过,另一半时间被困在前苏联的劳改营里。到1993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五,他已是70岁的老人了。并且他的面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二十多年劳改营严酷的生活环境摧垮了他曾经有过的强壮体魄。两条腿弯曲了,严重的关节疼痛每每在风雨之夜折磨得他无法入睡。胃也不好,总是莫名其妙地疼。在劳改营中经受二十多年折磨没有一个人的胃会是健康的。
萨布林大主教是在后半夜时分,被他的胃和关节共同联手,把他折磨醒了,去了趟卫生间,以后就再也无法入睡。窗外淅淅沥沥的秋雨声,如果没有病痛的折磨,那听起来应该像是一首诗,是诉说他坎坷而奇异的人生的一首诗,主基调沉重又荒谬。不过当一切苦难都已过去之后,回首往事居然还有那么多的东西叫人留恋和珍惜。
大主教早已看破生死。他甚至想过早一些结束自己的生命去见上帝。一生从没做过亏心事,尤其没有出卖过灵魂,他相信死后会进天堂。天堂里有多少快乐和幸福他没有过多考虑,只求上帝能重新给他个好身体。
3点15分,大主教刚要进入梦乡时,忽然间他觉得有一样什么东西顺着钟楼光滑的外墙在爬。也可能是错觉,他拿不大准,恍恍惚惚的。把灯打开后,除了淅淅沥沥的雨,再也听不出什么了。他打开了窗子。雨声骤然地大起来。黑幽幽的院子里,能看见亮晶晶的水洼。沿墙的几盏照明灯,都被树影遮住了。远处还有朦朦胧胧的街灯,昏昏欲睡的样子。不见一个人影,也不见一辆车。
大主教关上窗子,又重新躺下了。
大主教似睡非睡地又躺了两个多小时,6点钟时,他起来了。早起差不多是所有上了岁数的人的习惯。洗了一把脸,他走出了房间,要出去透透气。清晨到院子里散步,也是他的习惯,顺便也把院子里的落叶扫一扫。秋天了嘛,沿着院子的围栏,长着一圈的钻天杨。后院还有一棵挨一棵的桦树。
雨停了,这很好。但是要扫树叶是不可能了,一层层金黄色的叶子都被水泡上了。他沿着石头铺就的小径转了两圈,忽然觉得好像是缺了一点什么东西,却又想不起来是少了什么。人老了常犯这毛病。
修士瓦洛佳走出来了。瓦洛佳除了负责教堂里的事务,还担负院子里卫生的打扫和看护好苗米和苗姆两条狗……
倏地一下子,大主教想起他忘记什么了:每天清晨他一走出教堂的大门,苗米和苗姆必定摇着尾巴列队迎接他。它们先是立在台阶下面,把头仰起,好像在对他说,首长好。还等不及他还一句好,两个家伙已迫不及待地跃到他身边来,对他表示亲昵,用热乎乎的舌头舔他青筋凸暴的手。以后就一左一右跟着他散步。天天如此,从无例外。
萨布林四处张望,不见苗米和苗姆的踪影,便开始预感到有些什么不对头了,有一些紧张起来。这时正好瓦洛佳走到他跟前来,便问,苗米和苗姆在哪里?你昨天晚上没有把它们放出来吗?
瓦洛佳是狗的“监护人”,瓦洛佳说,昨晚他把狗放出来了,不会错的。萨布林又问,那怎么不见它们?瓦洛佳答,我也奇怪呢。
瓦洛佳说着就直奔后院去了。狗窝在后院。萨布林也跟了过去。
当他们跑到后院的时候,两条狗正躲在窝里,畏畏缩缩、一副犯了错误的样子。狗有这种天性,犯了错误它们自己知道,头低下去,情绪也不高,怕惩罚的样子。萨布林和瓦洛佳相互瞅瞅,都觉得这太蹊跷了,两条狗能犯什么错误呢?
瓦洛佳喊它们出来,喊了好几声,两条狗才耷拉着脑袋,很不情愿地走出了窝。在苗米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闪闪发光,镶着绿宝石和镂金的圣诞节彩蛋。
大主教和瓦洛佳面面相觑,两个人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
瓦洛佳从狗脖子上把那彩蛋摘下来,与大主教仔细辨认之后,两个人都感到背上咝咝地冒凉气。原来那个彩蛋曾是伊凡大帝的心爱之物,价值连城是不用说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本来在钟楼最顶端的密室里藏着,怎么现在跑到了苗米的脖子上呢?
感觉是共同的——那是一个让他们觉得不可能发生和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钟楼被盗了!
三
红星区刑侦支队小队长安德烈刚走进办公室,雨衣上的水珠还没甩干净呢,头儿就把他喊去了,对他说,伊凡大帝钟楼昨天夜里出事儿了,丢了什么东西,你去看看吧。
丢了什么呢?安德烈问。不过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断定自己要挨骂了。
头儿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头儿长得高高大大。在头儿的脏话还没有从嘴里甩出来之前,安德烈就一溜烟地跑出去了。
可当他逃到了楼梯上的时候,头儿的大嗓门甩出的语言炸弹,还是直追了过来:丢了什么东西?亏你说得出口。要是我什么都知道,还要你们干个屁!
头儿的脾气越来越坏,安德烈能够理解,1993年的俄罗斯,各种各样的案子如“雨后春笋”,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所以,无论是谁,想没脾气都难。
安德烈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纯种的俄罗斯人,而他,安德烈他“老人家”一眼看上去却像个中国人。黑头发黑眼睛是不用说了,鼻子也该大不大。于是同事们都喜欢叫他安德烈。正因为这一点很多同事经常开安德烈的玩笑:你母亲肯定有过外遇,而且外遇的对象肯定是个中国人。
还在少年的时候,安德烈就曾对自己的长相问题求教于母亲,但是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答案。倒是父亲的回答斩钉截铁:你母亲对我的忠诚绝对是百分之百的。
安德烈的长相问题给同事们平添了很多话题。还有一些同事们说:亲爱的安德留什卡,如果在生你之前你妈妈没有外遇的话,那肯定是遗传基因问题了,肯定是你奶奶的奶奶的奶奶,曾被拔都或拖雷的蒙古兵非礼过。当然了,如果身体强壮,也不排除你奶奶的奶奶的奶奶,非礼过人家蒙古兵小伙。一定是这样的。基因这个东西不一定非得直接就传下去,有时要隔几代才能显现出结果。
对于同事们的种种断言,安德烈都将信将疑。不过每当同事们把他的身世同那古老的东方相联系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都会升腾起一股神秘的感觉,崇高又甜蜜。当年读大学时,如果不是中苏关系正紧张着,他一定会选学外交和中文,以求将来有机会去中国转一转。心里话,他巴不得自己奶奶的奶奶的奶奶,被蒙古兵非礼过或非礼过蒙古兵,这样他去中国的理由就充分了:寻根。
马上奔三十的安德烈结过婚,但没过多久就离了。耍光棍的他每天的时光是这样度过的:早晨8点钟去上班,到晚8点也许更晚些才能回到家。每天6小时工作制和社会主义劳动健康保障法从来都没有被他认真执行过。到家后吃口饭,跟母亲说上几句话,看看电视,就准备睡觉了。不过,躺床上以后,他一定要把那本《俄汉口语对话》小册子翻上那么几页,才好安然进入梦乡。小册子是他在街头书摊上买的,中俄边贸热,这类简单会话的小册子很多。至于学它干什么,安德烈并没有认真地想过。他只是感到亲切。
安德烈人缘很好。领导对他的印象也相当不错。业务熟练是不用说了,从警十年却没染上任何不良嗜好,这相当不容易。他不吸烟、不酗酒,也不乱找女人,上班还从不迟到。不过,关于这一条,上班从来都是早到而不晚到,是优点还是缺点,值得商榷。
安德烈的同僚们,那些有经验的小队长们,都是宁可在大门外靠着,让日头晒着和让风雨淋着,也决不提前一分钟走进区警察局的大楼。小队长们的顶头上司大队长,永远都是谁先在他面前出现就把最苦最倒霉的差使交给谁。
安德烈不是不了解头儿的这个毛病,可他就是管不住自己的脚。所以挨骂对他来说简直就像“家常便饭”一般的正常。
四
开始的时候,安德烈并没有意识到伊凡大帝钟楼的窃案会对改变自己命运起到什么转折的作用。他是以一颗平常心接下这个案子的——盗窃案、杀人案、抢劫案、强奸案、诈骗案,当警察的每一天接触的不都是这些东西吗?但是命运这个东西谁也说不清楚,一些毫不起眼的事情往往就能够改变很多的东西。比如现在的安德烈,当他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他的命运已经在悄悄地改变。当然,那只是在无形中的……
查看完了现场,安德烈的心里基本上就有谱了。可是经验告诉他还是先不动声色为好。再说,好奇心也确实强烈地驱使他要借机看一看伊凡大帝钟楼到底藏了多少宝物和都是些什么宝物。开开眼总是好的,开开眼,将来退休了,没事儿干了,写回忆录时,就会增加不少精彩内容。
但是人家不给他看。人家——失主的代表修道士瓦洛佳明确告诉他,我们已经反复查看过了,您没有再看的必要了。我们只丢了一幅画,除此之外什么都没丢。
这让安德烈扫兴。
“一幅画?”他问,“一幅什么画呢?”
“费奥凡·格列克的作品,‘神的忧虑’。”
安德烈惊奇地“哦”了一声。他尽管对艺术不是内行,但费奥凡·格列克的宗教画价值连城却是一种常识。
“真品还是赝品?”他问。
瓦洛佳的眼睛瞪大了,一副被污辱了的样子:“先生您怎么可以这样问?如果是赝品的话,还有必要把您请来吗?”
安德烈故意不理不睬:“这么贵重的东西说没就没了,有什么能证明它确实被盗了呢?”
瓦洛佳终于被惹火了,连珠炮似地说出一番话来:这幅画刚刚于一个月前才转移到我们这里,经过了我们大主教的手,圣约翰教堂所有的神职人员也都看见了。我们把它藏在钟楼顶层的秘室里了。而现在它没了,不翼而飞了,这就是证明,您还要什么证明呢?难道要我们自己去把这画儿找回来再给您看,才算是证明吗?
安德烈满意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刚才你气了我一下,现在一报还一报,扯平了。不一会儿他又问了瓦洛佳一句:“除了一幅画,真的就再没有丢失别的东西?”
瓦洛佳很坚决地回答:“没有,真的没有。”
安德烈说:“这就奇怪了,盗贼完全可以顺手牵羊多拿走一些东西,比如宝石,比如夜明珠,他为什么就不拿呢?”
瓦洛佳摇头,说他也不知道。
安德烈又问他:“你怎么看这个案子?说说看,别有顾虑。”
瓦洛佳迟疑了一下,他当然明白安德烈话里的意思。
“从理论上讲,”他说,“盗贼应该是破窗而入。可实际上……”
“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安德烈接过他的话说,“给你个云梯,你也爬不上伊凡大帝钟楼的顶层——是这样吗?”
安德烈拍了拍瓦洛佳的肩膀,传达出去的信息很明确,我们警察可没把你当外人。其实安德烈心中早已有数,按照惯例来说名画失窃一定是内部人干的。内部人早瞄好了那幅画,抽冷子把它盗走了,为了转移视线,故意把钟楼的窗子打开,伪造出让人以为有盗贼进来了的样子。说真的,这种幼儿园水平的小伎俩安德烈见得多了。
安德烈单刀直入了,问瓦洛佳:“说说你的意见看,谁最可疑?”
瓦洛佳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谁都不可疑。”
安德烈说:“那就奇怪了,谁都不可疑,画儿怎么会没了呢?”
瓦洛佳圆睁的眼睛有一些茫然。他真的感到奇怪无比。
安德烈又拍了拍瓦洛佳的肩膀,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对他说:“我之所以问你,是为了加快破案的时间,你不知道也就算了。这也怨不得你,生活中有许多人外表是正人君子,实际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不过,无论他们怎样伪装,在科学的照妖镜面前都必将原形毕露。”
安德烈对瓦洛佳说:“你等着看我给你亮绝活儿吧。”
其实安德烈的绝活儿不过是指纹断案而已。手段平凡却十分管用,自从1905年苏格兰传教士亨利·福尔兹宣布了世界上绝没有两个人的指纹是一样的这个真理后,历时百年,完全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安德烈要把圣约翰教堂所有26个人的指纹全取下来,再跟窃贼的指纹两相对照,谜底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然而,百密一疏,安德烈大约忘了大主教是什么身份的人。教堂全部25个人的指纹都取下了,剩最后一个人时,遇到了麻烦,萨布林大主教死活不配合,还气得要死。他苍白的常年不见阳光的面孔由于激动都变得扭曲了。还拍桌子,颤巍巍鹰爪子一样的手指头指着安德烈嚷嚷,他的人格被污辱了。还说警察愚蠢,说我一个70岁的人了怎么可能自己偷自己?!你们这些警察,长着脑袋是干什么用的,光吃饭吗?
在整个分局里,安德烈可算几个脾气最好的警察之一了。很少有人见他发火。然而即便如此,大主教也让他动气了。随他去的两个帮手更是早已怒容满面。警察们是谁?什么叫警察?在安德烈的眼里,如果说还留有一点儿尊重的话,那仅仅因为萨布林是位70岁的老人。
但即便如此,有修养的安德烈仍是较好地展示了他的自控能力,没有马上采取行动,把大主教像按倒一只干巴老公鸡那样按倒,再把他的干巴鸡爪子拽出来,在印色盒上按那么一下子——没有,安德烈没有这么做。事后看安德烈这么做真是做对了。他给他的头儿打了个电话做请示,说大主教不配合怎么办?还顺便问了一句主教这一级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干部,科级还是处级?
头儿——那个早晨刚刚骂过安德烈的人,听罢安德烈的请示,回了一句话,吓得安德烈一哆嗦:
我告诉你安德烈,萨布林那老头别说你我,连卢日科夫都得让他三分。卢日科夫这个人你听说过吗?!
卢日科夫,大名鼎鼎的莫斯科市长,连三岁小孩子都知道,安德烈怎么会没听说过?
可是,安德烈分辩,他不让取指纹怎么办?
动动你的猪脑子!电话那一头吼。
撂下电话,安德烈觉得心里头舒服了不少。他就是这样一个怪人,每次挨骂心里都舒服。他有他的一套理论,上司骂你(尤其骂粗话)那是没拿你当外人。怕的是上司当面不骂你背后骂你,那你小子的末日就快到了。
上司一骂他脑袋当即就清醒了,一方面觉得自己该骂,一方面马上对他的一个手下耳语一番,让他开车快回局里一趟。
他又跟瓦洛佳闲扯,闲扯是耗时间。问人家瓦洛佳,你们这些修道士都不结婚,那么性生活怎么解决呢?
瓦洛佳的脸拉下来,显然对这样的话题不感兴趣。
“那好,我们换个话题,”安德烈说,“你们被盗的这幅画估计能值多少钱,大约?”
“少说一百万美元。”
安德烈着实吓了一跳。所谓费奥凡·格列克的宗教画价值连城,他原以为也不过是一个夸张的比喻,却没成想会值这么多钱。由此看盗贼不再偷别的东西,也不是没有道理。百万美元,够一个人活几辈子了。
手下回来了,跑得气喘咻咻。
安德烈重见大主教萨布林。重见的理由是道歉。笑,点头哈腰,还握了一下手。
请注意,握了一下手。
他的手心多了一块隐形小胶布,这个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小玩艺儿可以清晰无比地把对方的指纹“克隆”下来。轻轻一个动作就够。
如此,伊凡大帝钟楼26名神职人员的指纹,尽在我们可爱的聪明的黑头发却又是纯种俄罗斯人的安德烈的掌握之中了。
五
安德烈高兴得早了一点儿——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作案人的任何一点儿蛛丝马迹,就更别说指纹了。这也让他震惊和沮丧,因为这样一来采下来的26个人的指纹就等于说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使得我们可爱的安德烈的自信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于是他又一次提出,要看一看钟楼珍藏的那些宝物。这回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是为了寻指纹。没有窃贼的指纹,就没法与他已掌握的26个指纹做比对。
但他的要求再一次遭到拒绝。修道士瓦洛佳给出了很合理的解释——宝物分别藏在专门打造的柜子里,那些没有丢失的宝物都各自单独地放着,完好无损的锁头连被碰过的痕迹都没有。请问您看这些宝物有什么用呢?
其实看看总比不看好。但有了头儿的那些话,安德烈不敢态度强硬。寻思了一会儿,他问:“这么说费奥凡·格列克的传世名画确实是单独放着的了?”
瓦洛佳都有些不耐烦了。关于这个问题他已不知向安德烈说过多少遍了。不过他也不想得罪安德烈,再说人家毕竟是来帮你破案的嘛。
于是他只能又重复了一遍:“费奥凡·格列克的画,准备过几天拿到扎格尔斯克展出,这幅从来没有面世过……”
“请等一下。”安德烈制止了瓦洛佳,他感觉自己似乎抓取到了一点儿什么,“你说这幅画从来没有面世过,对吗?”
“是的。”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见过这幅画的人除了你们教堂里的,再没有外人?”
“也可以这么说,但海关人员应该是见过的。这幅画是海关罚没的。画从中国走私过来。”
“我们的画,我们国家的宗教名画,怎么会跑到了中国去呢?”
瓦洛佳端了一下肩膀,说:“那可一言难尽了。要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您只有亲自找我们大主教去谈了。”
安德烈不想去找大主教。一方面他不愿意看老头那张地狱样的脸,更为重要的是,他现在没有闲心像小朋友那样,拿个小板凳去坐着听一个老人讲一个絮絮叨叨的故事。他的任务不是要了解宗教名画从哪儿来,而是要搞清这幅画现在去了哪儿。
瓦洛佳看出了安德烈的难处。他忽然间想起了苗米和苗姆以及那枚曾挂在它们脖子上的圣诞节彩蛋,便把这个细节说给了安德烈听。
有这等事?安德烈听了果然吃惊。问瓦洛佳,这枚彩蛋如果拿去拍卖,能值多少钱,大约……
瓦洛佳说:“不会少于10万美元。”
安德烈又吓一跳,他一辈子也赚不了10万美元呀,于是情不自禁地问瓦洛佳:“你分析分析看,盗贼为什么不把彩蛋也拿走呢?”
瓦洛佳一端肩膀,“谁知道呢!”
“彩蛋是同那幅画放一起的吗?”安德烈问。
“当然,是要准备一块儿展出的。”
安德烈拍拍瓦洛佳肩膀:“走,带我去看看那两条狗。”
苗米和苗姆已恢复了常态。见到了安德烈一阵低狺,有扑上来要拼个你死我活的样子。这个细节更坚定了安德烈的信念,作案的一定是内部人,狗认识他。
他问瓦洛佳:“彩蛋在哪里?我需要看一看。”
瓦洛佳这一回没有拒绝。安德烈也就大有收获,他在彩蛋上取下了一个指纹。由此可以判断窃贼百密一疏,把彩蛋往狗脖子上挂时,摘下了手套。
安德烈高高兴兴地带着他的两个下属回局里去了。
不过,事实再一次让他失望了——从彩蛋上取下的指纹与钟楼26名神职人员的指纹相对照,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哪怕一点相像的地方都没有……
案件首次陷入了僵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