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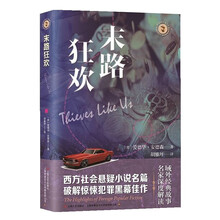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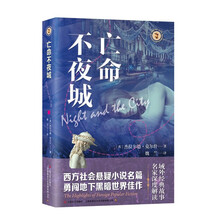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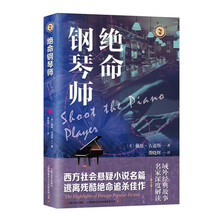



一年前,伊莎贝拉年幼的儿子深夜失踪,睡眠从此变成了她的梦魇。为了找回孩子,她开始调查身边一切可疑人物。随着调查不断深入,伊莎贝拉发现她曾经笃信的一切竟然暗藏层层罗织的谎言。
妹妹溺水的真相是什么?艾利森的死因真的是药物过量吗?她深爱着的丈夫究竟是深情还是惯于操控人心?
周遭的一切皆不可信,包括她自己的记忆……伊莎贝拉决心调查下去,无论真相终将通往何种结局。
电视机正隐隐约约地播报着正午新闻,我穿过房间去给自己煮咖啡,这将会是今天的第三杯咖啡。我昨晚洗了澡,换了衣服,但当清晨第一缕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时,我又从沙发上爬起来,走进浴室,打开淋浴喷头,仰起头,让水彻底淋湿自己。
然后我会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像之前尝试了无数次的那样,想象着溺水的感觉。
疲惫会对人的大脑产生一些奇怪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自从我睡不着觉以后,脑子里总是会蹦出和折磨人有关的东西,不是那种明显的暴力行为,诸如用生锈的刀片划过皮肤,或者用一把旧钳子夹张开的手指。我想到的,是那些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例如睡眠和食物,它们同样能把我们折磨得痛不欲生、孤独无助、感官失调、无法呼吸。
如今,我对这种感觉十分熟悉,我知道彻夜难眠,满脑子胡思乱想有多么让人崩溃。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不可能完全没有睡过觉,不然人早就撑不住了。有时候我会在候车室或出租车上打盹,睡醒后,看看表,才意识到自己并不知道上一个小时发生了什么。这些微睡眠有时仅仅持续了几秒钟,却属于深度睡眠,睡意强烈且毫无来由,似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又以同样快的速度消失不见。有时我躺在沙发上不停地打盹,每15分钟醒来一次,然后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刚开始的时候,哈里斯医生给我开了安眠药,让我每天晚上吃一片。我试过几次,但剂量太小,完全不起作用,于是我开始攒药。我会一次性吃三四片,直到眼皮终于重得抬不起来,可就算这样,我还是会在几个小时后突然醒来,脑袋昏昏沉沉的,行动迟缓,无法思考,什么都做不了。
有时候,尽管我们很努力地想要控制大脑,但总是徒劳无功。
这会儿,我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捧着杯子,盯着面前那个信封,这是我昨晚从那个拿着节目单的男人手里夺过来的。不知道妓女收钱时是不是和我一样尴尬,毕竟,我也是为了得到些东西才在这么多人面前抛头露面的。
虽然我出卖的不是身体,而是灵魂,但这种感觉更令人崩溃。
我喝了一口咖啡,伸手把信封翻了过来,解开信封上的细绳,把里面的东西倒到桌子上。这就是我的报酬——一份完整的观众名单,这里面包括每位购票者的姓名和电子邮件地址。梅森案的主办警官曾告诉我,罪犯们经常会出现在案件的新闻发布会上,或者受害者的纪念活动等公共场合,重温犯罪时的快感,享受逃脱制裁的侥幸,或者了解案件的最新进展。按照这个逻辑,只要是自己参加的会议,我都会要求主办方给我提供与会者名单,希望能从中发现一些可疑的人。每当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时,主办方都会拒绝我,声称这侵犯了观众的隐私。但我会立刻指出,这些观众在参加活动时,早已在相关条款和协议中同意公开他们的信息了。
当然,这些都是写在协议的细则里的,永远用小号字体打印的细则,那样最容易被忽略。
最终,这些主办方都会妥协。因为梅森的案子备受关注,所以即使案件目前没有什么进展,但警方依然没有放弃。也因此,像我这样的演讲者,每次出场费都要几千美元。可我不要钱,我只要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会给我提供一些线索,任何与案件有关的线索,我都不会放过。
我扫视着名单,这些人的名字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
亚伦·皮尔斯、阿比盖尔·费希尔、亚伯拉罕·克拉克、亚当·施雷德。
接下来我会进行一系列操作:在社交网站上搜索这些人的名字,仔细翻阅他们的个人资料,试图推测他们的住址。我会重点关注几类人:没有孩子的女性,养很多猫且很闲的独居者,或是看上去就令人怀疑的男性,以及那种眼神凶狠冰冷、让人不寒而栗的人。
亚历山大·伍德沃德、艾丽西娅·布赖恩、艾伦·拜尔斯、贝利·迪恩。
之后我会登录到性犯罪数据库网站,看看这些人是否有过犯罪记录。一旦发现任何可疑的点,就在名字下面做标记。诸如此类,往复循环。
这是一项枯燥而又乏味的工作。但没有嫌疑人,也没有任何线索,这就是我现在的处境。这些枯燥的事,是我唯一能做的了。
这些名字中有些看着很眼熟,我知道我曾经搜索过。一段时间后,有些名字会不断重复出现,他们是这类节目的常客。不知怎么,他们总会找到我,有的会再次介绍自己,有的则认为我应该记得他们。他们期待我能解答他们的疑问,或参与他们的讨论,好像我是他们读书俱乐部的作家似的。
我想我应该问问他们对我的遭遇有什么感想,对一团乱麻的案件有什么头绪,对发生的一切有什么看法。
我说话的时候,他们会用手轻轻扶着我的胳膊,似乎在担心我会随时随地崩溃,这样的举动真让我抓狂。他们的头会像好奇的小狗一样歪着,声音总是低几个八度,让我不得不靠近一些才能听清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耳朵下面的甜腻香水味,以及嘴巴呼出的难闻热气都让我反胃。
谈话结束时他们会说:“我简直无法想象你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没错,他们无法想象。这种感觉除非亲身经历,否则没人能感同身受,但真的经历了,一切都来不及了。
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变成了受害者。
罗斯克在我脚边睡着了,我能听到它均匀平缓的呼吸声。它会时不时抬头朝门口看,项圈上的狗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突然,它站了起来,跑到窗边坐下来。窗外闪过一个黑影,我心里一沉,紧紧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把手放在胸口,手指隔着衬衫摩挲着项链,然后朝门口走去。
不敲门我都知道是谁。
“早上好。”打开门,我才意识到现在已经是中午了,门口站着的,是我的丈夫,“没想到你会来。”
“嗨,我能进来吗?”他说话时,眼神一直在回避我。
我打开门让他进来,可他生硬客气的样子,仿佛我们是两个陌生人,好像他从来未在这栋房子里生活过,从未亲吻过我的每寸肌肤,也从未抚摸过我的每个胎记和疤痕。他俯下身轻轻拍着罗斯克,嘴里不断小声重复着“真乖”。我看着他们之间如此平静、自然的互动,真心希望罗斯克能龇起牙冲他狂吠。因为他抛弃了它,也抛弃了我。
但罗斯克只是舔了舔我丈夫的指头。
“你来干什么?”我双臂交叉,紧紧抱在胸前。
“我来看看。今天这个日子……你知道的。”
“嗯,我知道。”
今天,是第三百六十五天。距离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儿子,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一年前的今天,我给他讲了睡前故事,掖好了被子,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基本的旁边,闭上了眼睛。我就那样轻易地进入了平静而悠长的幸福梦乡,浑然不知黎明时分,地狱之门会悄然向我们敞开。
“还是睡不着吗?”
我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我知道他没有别的意思,但即便他没有,我依然讨厌他这么说。
“你怎么知道?”
我努力挤出一个微笑,想告诉他我是在开玩笑。但我不确定自己挤出了什么表情,也许看起来疯疯癫癫的,因为他并没有笑。
一开始我不敢合眼,是怕梅森突然回来了,毕竟他是被人带走的。梅森被人带走的时候,我竟然在睡觉,世界上怎么会有我这样的妈妈?我应该有预感的,我应该能感应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正在发生,但是我没有,我没有任何感觉。所以开始那几天,我告诉自己,我得醒着,万一呢?或许半夜的时候,我去他的房间偷偷瞄一眼,会看见他直直地坐在自己的小床上,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他会发现我在偷看他,开心地冲我笑,然后将手伸向我,手上还紧紧抓着自己心爱的毛绒玩具。
为了看到这样的场景,我想保持清醒,不,我必须保持清醒。
几天变成了几周,几周变成了几个月,梅森依然杳无音讯。但那时起,我不再是从前的我。我变了,大脑里的某些东西突然断裂了,就像一个崩到极限的橡皮筋,再也无法承受一丝一毫的张力。最开始的时候,本曾苦苦哀求我,试图拽走那个半夜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直勾勾望着窗外黑夜,毫无睡意的我。
他对我说:“你这个样子没有任何意义。你需要休息,伊兹。”
我知道,他说得没错,这样做确实没有任何意义。但没有办法,我控制不了自己,我真的睡不着。
“工作怎么样?”他努力地找着话题。
“进展缓慢。”说着,我把一缕头发别到耳朵后面,因为没有用吹风机吹头发,这缕软软的头发一直散在我额头上,痒痒的,“目前我没有收到很多工作邀请。”
“我觉得现在机会应该会相对多一点。你懂的,媒体的作用。”说着,他走到沙发旁边坐下。我有些生气,因为他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坐下了。不过,这个沙发确实是他掏钱买的。
“我不想利用媒体。”
“这和你现在做的事情有什么区别?”
我瞪着他,他也瞪着我。这才是他今天来这里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他肯定是从哪里听说了我的演讲,我明白他迟早会知道,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你为什么不直接说你想说的?说啊,你倒是说啊!”
“好,我说。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想让警察放弃他的案子。”
“没有放弃!”他愤怒地喊着,“伊莎贝拉,警察一直在努力寻找线索。”这样的对话我们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了。
伊莎贝拉。他已经不再叫我伊兹了。
“你必须停止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所有的事。”说着,他朝着餐厅走去。我注意到他刚进门时朝那里瞥了一眼,经过那个拐角时,他的眼神下意识地闪躲,好像随时准备挨一拳一样。他的眼睛扫过墙上那些贴得乱七八糟的照片,那里曾经挂着我们婚礼的油画。“这有点病态,而且,看起来……”
“看起来怎么了?请你告诉我。”我打断了他,一股怒火在胸腔里燃烧。
“看起来不对劲,”他一边搓着手,一边说,“你,在儿子失踪整整一年的前一天,站在一帮心理变态的观众面前讲这个事情,这一点都不正常。”
“那你告诉我,本,我应该做些什么?怎么才算正常?什么都不做吗?”
我瞪着他,指甲用力地抠着手掌心。
“这些都是一无所有的人,他们没有家庭,本。罪犯现在还逍遥法外,带走我们儿子的人……”我停下来,使劲咬住嘴唇,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深呼一口气后,我继续说下去,“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点也不在乎,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想快点找到他。”
本突然从沙发上弹了起来,他的脸涨得通红。我知道我说得太过分了。
“我不许你那么说!”他用手指着我,愤怒地吼道。他的嘴上挂了一串唾沫,正随着嘴唇的抖动上下颤动着。“你凭什么说我不在乎?你根本不明白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有多大,他生前也是我的儿子!”
“去掉那两个字。”我轻声纠正他,“他现在也是你的儿子。”
我们陷入了沉默,隔着客厅凝视着彼此。
“也许他还活着呢。”我的眼泪再次溢满了眼眶,“或许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还……”
“伊莎贝拉,他已经不在了,不在了。”
“他可能……”
“不可能。”
本叹了口气,把手插进头发里,从额头一直捋到脑后,然后他走过来,抱住了我。我没有力气拥抱他,只是站在那里。如同行尸一般。
“伊莎贝拉。”他用手指轻抚着我的头发,在我耳边轻声说道,“我不想反复跟你争论这些,真的。这件事也让我痛苦不堪,但你越早面对现实,就能越快回到平静的生活中。你必须尽快走出来!”
“一年,才一年你就能忘了吗?”
“我还做不到,但是我在努力,努力让自己走出来。”本说道。
我安静了下来。他的手放在我的脑后,耳畔是他温暖而潮湿的呼吸,隔着胸膛,我能隐约感觉到他的心跳声。我刚张开嘴准备道歉,他却突然松开了手。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他放下手臂,“这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