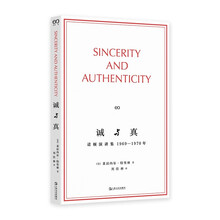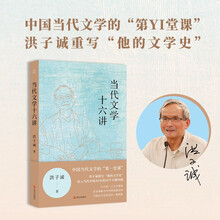第一章 横空出世:文化激进主义与新文学的倡导
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并没有促成一种具有崭新形态和面貌的文学样式出现。尽管近代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和打破了根深蒂固的文学传统和审美规范,但它与传统文学的“脐带”尚未彻底地撕开和断裂。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只有以1915年《青年杂志》(自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创刊为开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才以彻底的“断裂性”姿态从根本上破坏和动摇了传统文学的牢固根基,从而创造出了独具一格、别开生面的中国新文学。总之,五四时期是文学革命的时代,它大胆地引进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和理论学说,激进地批判和否定中国传统的封建旧文学,推进了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一、革命与改良策略的交响
中国文学在五四时期能够顺利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乃借助于“五四”激进文人革命激情的全面喷发和无比威力,而直接倡导中国新文学并推动其蓬勃发展的则首推激进文人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凭借《新青年》这一生龙活虎的传播媒介,中国文学首次以激进的“革命”方式在文学历史的长河中绽放出靓丽的青春风采。
在学界看来,1917年1月和2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和第6号上的先后发表,标志着五四文学革命的正式发端。在文学革命的运思方式上,胡适和陈独秀虽然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但总体来看,他们的并不含有暴力、暴动倾向的革命姿态,却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彻底颠覆和全面背叛。
作为文学革命出色的拓荒者,胡适最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正如陈独秀所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然而,随着学界对胡适正面历史价值的不断定性,反而对其撰写的可以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经典的《文学改良刍议》的认识存在更大歧义。一个比较突出的观点是认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并无“革命”的内涵,是陈独秀把它粗暴地改为带有政治色彩的“革命”。看起来这种反思不无道理,但触摸历史脉搏它却经不起诊断和推敲。实际上,胡适的“革命”意念由来已久,“革命”本来就是《文学改良争议》的题中之旨、文中之意。它响亮提出的“八不主义”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彻底性革命和根本性破坏,其宣告的文学的终结和新文学的来临,足可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
我们知道,留学美国期问的胡适早在1915年夏秋就开始了中国文学革命的思考,产生了除旧革新的愿望。同年8月他撰写的《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提出了文言文是半死的文学、白话文是活的文学、文言是死的语言、白话是活的语言的论断,萌发了文学革命的思想。同年9月,他则在为同学梅光迪去哈佛大学所作的一首白话诗中首次公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构想。虽然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没有得到同学和朋友们的赞同,但胡适在与他们的争论、辩驳中越来越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弊端;越来越清楚了自己的主张、建议的革命性意义,也越来越坚定了自己文学革命的信念,并大胆宣称“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1916年8月19日,在致朱经农的信中,他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建设新文学的八项要点。到这个时候,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应该说已经形成了纲领性的意见,达到了理论形态比较成熟的境地。同时,胡适即给国内的陈独秀写信,正式提出了上述文学革命的八项条件。陈独秀非常高兴,不仅将胡适之来信刊载于1916年10月第2卷第2号的《新青年》上,而且很快复信给胡适,认为胡适所提出的“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极力夸赞它“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同时希望胡适“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
然而,胡适正式以理性的眼光、学理的态度撰写《文学改良刍议》回应陈独秀的时候,却将“文学革命”置换成了“文学改良”。个中原因,胡适曾经有如下一段真情告白,他说:“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并认为:“这是一个外国留学生对于国内学者的谦逊态度。文字题为‘刍议’,诗集题为‘尝试’,是可以不引起很大的反感的了。”
从理论上讲,我们应该尊重当事人就事论事的观点,但我们不能为当事人的自述所迷惑,而应该从其表面言辞深入其内心实质,捕捉和挖掘当事人言辞之中隐藏的深层心理动机。就笔者的理解而言,在国人普遍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的情境之下,胡适将“革命”置换为“改良”,认为“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指出“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等诸如此类的表白,并不代表胡适文学革命立场的软弱和妥协,实际上乃不失为一种有胆识、有见地、有眼光、有分寸的革命策略。远在异国他乡的胡适,在陈独秀给予他发表言论机会之际,之所以不敢公开张扬革命而低调处理自己的文学革命意向,自然与胡适自身向来对于“革命”的理解和认识密切相关。以进化思想、实用主义作为理论支持的胡适,并不认为“革命”是对过往的激进否决,而是把“革命”视做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他说:“历史的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这种置换策略吻合胡适本人“处之以温和,持之以冷静”的精神气质和温柔敦厚的性格情状。即使刚毅果敢如鲁迅者,也觉得胡适的做法具有可行性。他说:“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叫不过我们也要同鲁迅那样“想一想”,胡适这种花样的韬略究竟是什么?胡适说“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可能仅仅只是中国文字上变化的一种花样罢了,并非真的就颠覆或消解了“文学革命”的深层用意。其实,在胡适的“仓库”里,“刀枪”有的是。一待陈独秀大胆地掀开了他改良面纱遮掩着的革命旗帜之后的次年,决心在破坏的基础上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胡适,便勇敢地接过了陈独秀果敢竖起的“革命”旗帜,或者说又继续了他自己原初的“革命”路径,随即写出了大胆断言中国“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的名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该文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一文标题的唯一区别,就是添加了“建设的”三个字,因此表面上看可以说是挪用了陈独秀文章的标题,而实质上表示胡适对陈独秀规划的文学革命方案和激进的文学革命精神的高度认可和赞同。胡适认为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就“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这样就“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字。”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