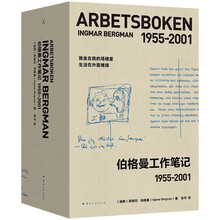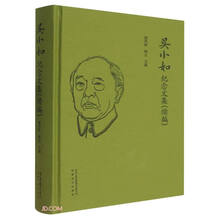导言
叶廷芳
20世纪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世纪,是一个大动荡、大破坏的世纪,也是一个大变革、大创造的世纪,无论政治与社会,还是科学与技术,抑或文化与艺术无不如此。就以西方文学而论,这一个世纪就划了两个时代:“现代”和“后现代”,围绕它们涌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多的流派,也产生了一大批相应的大师级作家,他们以崭新的面孔迥异于以往的同行,并以经典地位载入史册。为本书冠名的弗兰茨?卡夫卡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享有“现代文学之父”的美誉。
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生长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但他属于奥地利作家,因为19世纪6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这段时间,捷克归入由奥地利主宰的、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奥匈帝国”的版图,故这一时期布拉格有相当多的人能操德语,并有一座德语大学,卡夫卡就是在德语大学学成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因此他接受的是德意志文化,一生都用德语写作。
卡夫卡离开校门后,经过一年的实习就于1908年起供职于劳工工伤保险公司,直到1922年病退。而在办公室“恪尽职守”的卡夫卡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写作,所以卡夫卡始终是一位业余作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靠剥夺睡眠时间换取创作可能的业余作家,后来成了他那个时代顶尖级的大家。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但奇迹还表现在奥地利这个现在的人口只有800万的小国,在上世纪产生了差不多足够“一打”的世界级的文学大家,这个数目不仅超过了德意志文化的中心——德国,而且超过了同时代的世界上任何国家!应该说,首先是“奥匈帝国”的政治与社会的现实,决定了这一现象的产生。同时,当时欧洲的艺术文化思潮也对这一现象起了催化作用。
卡夫卡创作的旺盛时期(1912~1922),正值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表现主义运动方兴未艾之时(1910~1924)。德国(准确地说是德语国家,包括奥地利和瑞士德语区)的表现主义运动既是一次思想反抗运动,也是美学变革运动,对20世纪的德语文学乃至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就美学变革而言,这场运动深刻地经历了“反传统”的过程。它剧烈地颠覆了在欧洲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模仿论”美学,而代之以“表现论”美学,即把艺术创作习惯于对客观世界的描摹,转向对主观世界的表现;从强调外部的真实,转向内在的真实。这股“向内转”思潮对卡夫卡的创作起了决定性作用。从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来说,他是积极参加了的。这场运动的一位重要作家、活动家,也是领袖人物的弗兰茨?韦尔弗也生活在布拉格,卡夫卡与之保持频繁来往,两人经常讨论文学中的问题,因而成了要好的朋友。表现主义最为推崇的两位思想家尼采和弗洛伊德,也引起卡夫卡的关注,尤其是尼采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对卡夫卡起过重要影响,有人甚至把尼采看作卡夫卡的“精神祖先”。再从卡夫卡的创作看,也留有表现主义的许多特征。诸如表现主义所强调的内在真实,所追求的梦幻世界,所爱好的怪诞风格,所崇尚的强烈感情,所习用的酷烈画面等等,都在卡夫卡作品中烙下鲜明的印记。不了解表现主义的美学特征及其与卡夫卡创作的关系,就不可能很好理解卡夫卡的作品。
但如果在阅读卡夫卡作品的过程中过于拘泥于表现主义,那也会产生误差。正如德语现代文学另一位滥觞于表现主义的领军人物布莱希特许多地方超越了表现主义一样,卡夫卡也不是任何一个主义所概括得了的。事实上后来的超现实主义诗歌、荒诞派戏剧和黑色幽默小说等都向它攀亲结缘,说明卡夫卡与20世纪的西方文学的关系,一如毕加索与20世纪的西方美术然。要探悉这一现象的奥秘,最根本的一点是看他的创作态度。他不是把文学创作看作单纯的审美游戏,而是表达自我的手段。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内心有个庞大的世界,不通过文学途径把它引发出来,我就要撕裂了!卡夫卡凭着他那圣灵般的智力,分明洞察到人类存在的危机,即那日甚一日的“异化”趋势,他急欲向世界敲起警钟,对人类生存状态及其合理性提出质疑。因此直到晚期他还在日记里写到:他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通过文学途径“将世界重新审察一遍”。无怪乎他于1922年写的《城堡》第一稿是这样开头的:主人公急急忙忙要求旅馆里的一位侍女帮他的忙,说他有个十万火急的任务,一切无助于这一任务的想法和行为他都要加以“无情镇压”。没错,生活中他正是这样做的。你看他,“对无助于创作的一切我都感到厌恶”,甚至“一个男人生之欢乐所需要的一切”他都放弃了,包括婚姻、家庭,甚至健康。为什么后来他把这一稿作废了呢?原来他已病入膏肓,感到要完成“重新审察世界”的任务已经“来不及了!”
现代文学,尤其是与存在哲学相关的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一个明显区别是,它不再把创作看作是纯美学的事情,而看作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燃烧的过程。(为什么卡夫卡晚年要嘱告他的朋友,在他死后把他的作品统统“付之一炬”?他在乎的就是他的写作过程,而这过程他已经有过了。)因此你看卡夫卡,他在写作时完全处于身心交混的“忘我”状态,他的短篇小说往往是一个不眠之夜“一气呵成”的产物,是“一夜的魔影”。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生存体验,一种从深心中发出的生命呼叫!无怪乎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特别是那些有代表性的长短篇小说中,往往晃动着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分明是作者自己的身影。但这不是报告文学的主人公,而是艺术化了的人物形象——像他,又不像他。原来作者把自己捣碎并融和在里面了!这就不难理解,他的作品何以有着如此入木三分的真实,一种任何写作高手凭经验和技巧都“创作”不出来的真实!这就是卡夫卡的独特性,这就是出身于表现主义而又胜于表现主义的卡夫卡。
卡夫卡诚然不是哲学家,也没有用任何理论语言阐述过他的哲学观点。但卡夫卡无疑是一个富有哲学头脑并紧张地进行哲学思考的文学家。他用艺术语言所暗示的人类存在的焦虑及有关的一些根本问题,与哲学家们,尤其是存在哲学家们通过理论语言所阐明的观点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的。这也就是说,他把哲学引进了文学,并使二者成功地融合为一。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之前,存在哲学的创始人克尔恺郭尔和稍后的尼采引起他那么大的震动,在他之后,他在另一拨哲学家如萨特、加缪等人那里那么受青睐。所不同的是:所提及的这些哲学大师几乎都可以说是哲学家兼文学家,但我们不能说卡夫卡是文学家兼哲学家。因为前者是有意识地让哲学去“勾引”文学,使文学成为哲学的嫁娘和附庸,而后者则是将哲学提炼为文学的精髓,使之成为文学血族里的精神支撑,因而使文学更强壮、更尊严;同时,他把哲学变成了美学,使文学哲学融于一体、难分彼此,不仅受到文学家的推崇,也受到哲学家的敬重。这是卡夫卡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
任何时代的美学变革首先是由那个时代新的精神、新的生存方式和新的文化理念引起的,20世纪的美学变革也不例外,在这一问题上文艺依然遵循着“内容决定形式”的总规律。卡夫卡对存在所独有的那种体验,那种异化感和荒诞感,蒙在现实表面的那层厚厚的覆盖层,使语言失去了其固有的传统功能,而产生“失语症”。因为在他看来,那种照相式的写实“不过是铁制的窗板”,阻断人们去洞察那藏在表面底下的真实。而他要求于创作的是“传达一种不可言传的东西”,是放纵地“同魔鬼拥抱”的行为,是挖掘那种“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也看不到的东西”……为此他必须寻找新的表现方法。于是,用于影射和暗示的象征、譬喻的手法;引起联想和比附的梦幻手法;用以揭示假里藏真的荒诞手法;让人惊异、发人省醒的怪诞手法;制造亦真亦假、似假还真的悖谬手法;令人含泪而笑的“黑色幽默”手法等等,都纷纷到卡夫卡那里去报到了。无怪乎,德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兼文学史家汉斯?马耶尔说:卡夫卡在“从文学外走到文学内”的过程中,他“改变了德意志语言”。这就是说,卡夫卡成功地抛弃了德意志语言的习惯用法,而建立了崭新的审美概念,从而使德意志语言改了向,转了型。因此,卡夫卡对文学观念和形式的变革是划时代的。
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艺术革新,最初都只有少数先驱者为其献身。当他们刚刚捕捉到属于时代的审美先兆的时候,就义无反顾地进行实践和试验。从常规看,这种努力成功的几率很小,而失败的可能很大。正如美国美学家桑塔耶那说的:“1000个创新里头999个都是平庸的制作,只有一个是天才的产物。”一个艺术革新者为探索所需要的勇气和付出的代价,往往不亚于一个科学探索者。即便是那极个别的成功者,也未必马上就能获得鲜花和荣誉的报偿,以致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世界文学史上的“千年一帝”,由于他不顾当时流行的关于悲剧和喜剧的艺术教条,不但生前得不到桂冠,死后还被冷落了一个多世纪!至于像莫里哀这样的艺术教条的异端,若不是国王怜惜他的过人才华,恐怕连性命都难保。 直到20世纪,乔伊斯还曾为他的《尤利西斯》吃过官司。可见,美的探索者也像真的追求者一样,在一种时代的审美信息普遍觉醒之前,他注定要经历一段寂寞或孤独时期,甚至遭受残酷的迫害。卡夫卡生前发表的那四本薄薄的小册子,已经包括了他几乎所有的代表性短篇作品。但直至他死后多少年,世界始终报之以沉默!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和大量的睡眠时间;被剥夺的几十年宝贵寿命(刚过不惑就离开人世了);他始终憧憬的婚姻和家庭——这一切都因为写作而被他自己“无情镇压”了!很清楚:他为了“灵”(艺术)的至圣至美,付出了“肉”(生命)的彻底牺牲。因此我认为,像卡夫卡这样的时代先驱不仅是一位艺术的探险者,而且是一位艺术的殉难者。卡夫卡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刻画的两位动人的艺术家形象,即《饥饿艺术家》和《女歌手约瑟芬,或鼠众》中的主人公,就是艺术殉难者的自画像,也可以说是作者的自我写照。
卡夫卡作品中涉及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即“异化”(Die Entfremdung),这个概念首先出现在19世纪一些大哲学家的笔下: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等。马克思在批判地消化了前两位哲人的观点以后,沿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的思路对这一概念作过如下的概括:“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马克思《资本论》第六章初稿,转引自《新德意志报》文化周刊《星期日》1963年第31期)显然,新的哲学概念的这些创始人已经注意到社会化的机器生产的出现给人的生存造成的威胁:他们由对生产过程的支配地位变成了被支配地位。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兴起以后,“异化”概念的内涵大为伸延,仿佛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努力都在向自身利益和愿望的反面转化,从而导致人的生存陷入更为全面、深刻的危机和困境。
这一哲学思潮反映在文学中呈现出各种面貌,概括起来看,表现在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中,要么人不接受世界,要么世界不接受人;表现在人的自身矛盾中,是人的自我失落与迷惘。卡夫卡在理论上对“异化”没有发表过什么看法,偶尔使用“异化”这个词时,也不作“异化”,而作“疏远”解。然而卡夫卡的作品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所显现的世界,正是哲学家们想阐述的“异化”世界:作品中人的那种陌生感、孤独感、恐惧感、放逐感、罪恶感、压抑感;客观世界的那种障碍重重的“粘糍”性,那种无处不在的威权的可怖性,那种作弄人的生命的“法”的滑稽性,那种屠害同类的手段的凶残性……正是哲学家们想要描绘而不能的令人沮丧的世界。无怪乎卡夫卡的作品首先在两位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和加缪——那里引起强烈的共鸣,以至卡夫卡的名字在萨特笔下成为被提得最多的作家之一。
卡夫卡创作风格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荒诞感,这又是跟当代的存在哲学相联系的。按照存在哲学的观点,存在的本身就是荒诞的。如上所说,有异化感的人不接受这个世界,当然世界也不承认他。难怪卡夫卡的一位女友曾说,卡夫卡对周围的一切常常表现出惊讶的神情,就像一个赤身裸体的人处在衣冠楚楚的人群中那样尴尬。他的这一生存体验使他自然而然地把“荒诞”这一哲学概念变成美学。所以他的作品中往往出现一种似有若无、似实还虚、似是而非、若即若离的幻境。你看他的长篇小说《城堡》中的那座城堡,它分明坐落在眼前的那座小丘上,然而主人公想要走近它,却折腾一生也徒劳!难怪他在笔记中这样慨叹:“目标虽有,道路却无;我们谓之路者,乃彷徨也。”卡夫卡的这一创作特点在尔后的法国荒诞派戏剧那里得到发扬和提升,达到荒诞艺术的极致。荒诞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亦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各类文艺创作中被广泛使用。
在阅读卡夫卡作品的时候,有一个关键词必须注意,即“悖谬”(paradox)。这是卡夫卡的思维特点,也是他的重要艺术秘诀之一。悖谬,一个事物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与互相抵消。这本来是一个哲学概念(哲学中一般叫悖论),它贯串在卡夫卡的思想、生活与行为之中。同时,他也把它变成美学,体现在他的创作之中。他分明说,他生就的只有弱点,以致任何障碍都能把他摧毁(很像是),但他在别的场合却又说,他内心中有一种坚不可摧的东西(确实是);他那么渴望婚姻与家庭,三次订了婚,却又三次解了约;他视写作为生命,最后又要将他的全部著作“付之一炬”;他一生中都与父亲不和,在那封有名的《致父亲》的长信中谴责父亲“专制有如暴君”,最后却又对父亲表示同情,以致连那封信都没有交出去……他似乎总是不停地在建构,又不断地在解构——他到底是谁?
当悖谬变成美学的时候,在他的创作中构成一种“黑色幽默”式的悲喜剧情趣,读后让人感到一种“引起愤怒的明了性”(卢卡契)。《城堡》的主人公一心想进城堡,不过想开一张临时居住证,奋斗一生而不得,临死的时候,却又同意给他了!再看《在法的门前》那位乡下人,苦等一生也不让进,到快死的时候,又说这大门就是为他而开的!在《饥饿艺术家》中,主人公——一个以饥饿为表演手段的“艺术家”对艺术的无限追求与他有限的物质生命互相发生矛盾,于是在他的艺术达到“最高境界”之日,却是他的肉体生命彻底毁灭之时!这是“灵”与“肉”在悖谬中互相抵消。在同一小说末尾,一个瘦骨嶙峋的生命在马戏团的铁笼子里消失了,但一个强有力的生命、“每个牙齿都充满了力”的年青小豹正在发出猛烈的嗥叫。这是生命形态的互换。在《变形记》的结尾也有这么一景:变成甲虫的儿子以消瘦不堪的空洞躯壳在父母眼皮底下消失了,但在紧接着的郊游中,父母很快就欣喜地看到,女儿正以一个体态丰满的姑娘焕发着青春活力……在当代外国作家中,有相当多的人从卡夫卡的悖谬艺术中受到启示,在各自的创作中取得巨大成功,如美国的约瑟夫?海勒等黑色幽默小说家,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前苏联的小说家阿赫马特夫和戏剧家万比洛夫以及卡夫卡的同乡和崇拜者昆德拉等都是。
卡夫卡是以创作态度严肃著称的。除了小说,他的书信、日记、随笔、杂感、箴言等都写得极为认真,它们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文献和美学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构成卡夫卡创作的重要有机部分。其中书信占了卡夫卡全集的五分之二,而那些情感充沛、文采斐然的情书又占了全部书信的三分之二。所以书信成了本书三个板块中的重要一块。但愿读者朋友们能从卡夫卡的作品中汲取思想和艺术的有益养料,充实和丰富自己的文学知识,激发创作热情,提高艺术水平。
2007年1月北京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