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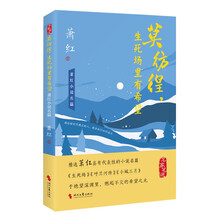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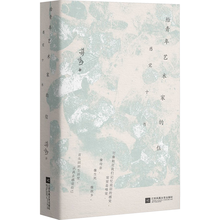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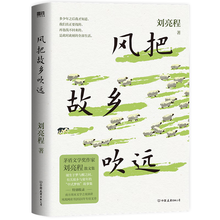
人类如要生活,依然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生活在天上啊等问题,必须抛弃。人类的心神哟!别张开翅膀,飞到天神那边去,而忘掉这个尘世呀!我们不都是注定着要遭遇死亡命运的凡人吗?上天赐给了我们七十年的寿命,如果我们的心态太高傲,想要永生不死,这七十年,确是很短促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地稍为平静一点,这七十年也尽够长了。一个人在七十年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享受到很多的幸福,要看看人类的愚蠢,要获得人类的智慧,七十年已是够长的时间了,一个有智慧的人如充分长寿,在七十年的兴衰中,也尽够去视看习俗、道德和政治的变迁。他在那人生舞台闭幕时,也应该可以心满意足地由座位立起来,说一声“这是一出好戏”而走开吧。
我们是属于这尘世的,而且和这尘世是一日不可离的。我们在这美丽的尘世上好像是过路的旅客,这个事实我想大家都承认的。即使这尘世是一个黑暗的地牢,但我们总得尽力使生活美满,况且我们并不是住在地牢里,而是在这个美丽的尘世上,而且是要过着七八十年的生活,假如我们不尽力使生活美满,那就是忘恩负义了。有时我们太富于野心,看不起这个卑低的,但也是宽大的尘世,可是我们如要获得精神的和谐,我们对于这么一个孕育万物的天地,必须有一种感情,对于这个身心的寄托处所,必须有一种依恋之感。
所以,我们必须有一种动物性的信仰,和一种动物性的怀疑,就把这尘世当做尘世看,韬洛(Thoreau——美国十九世纪作家和自然主义者)觉得自己和土壤是属于同类,具有同样的忍耐功夫,在冬天时,期望着春日的来到,在百无聊赖的时候,不免要想到,寻求神灵不是他的份内事,而应由神灵去寻求他;依他的说法,他的快乐也不过和土拨鼠的快乐很相似,他这种整个的大自然性也是我们所应该保持的,尘世到底是真实的,天堂终究是飘渺的,人类生在这个真实的尘世和飘渺的天堂之间是多么幸运啊!
凡是一种良好的、实用的哲学理论,必须承认我们都有这么一个身体。现在已是我们应该坦白地承认“我们是动物”的适当动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的真理成立以后,自从生物学,尤其是生物化学获得极大的进展之后,这种承认是必然的。不幸我们的教师和哲学家都是属于所谓知识阶级,都对智能有着一种特殊的,专家式的自负,致力于精神的人以精神为荣,正如皮鞋匠以皮革为荣一样,有时他们连“精神”一词也还觉得不够飘渺抽象,更拿什么“精粹”“灵魂”或“观念”一类的词字冠堂皇地写出来,想拿它来恐吓我们,人的身体便在这种人类学术的机器中,蒸馏成精神,而这种精神进一步凝聚起来,再变成一种精粹的东西。但是要晓得即使是酒精也须有一个“实体”——和淡水混合起来——才能味美适口,然而我们这些可怜的俗人却须饮这种精神所凝聚的精华。这种过分着重精神的态度实是有害的。它使我们和自然的本能搏斗,它使我们对于天性无从造成一种整体完备的观念,这是我批评它的一个主要点。同时这种态度对于生物学和心理学,对于感官、情感,尤其是本能,在我们生命上所占的地位,也是极少认识的,人类是灵与肉所造成,哲学家的任务应该是使身心协调起来,过着和谐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