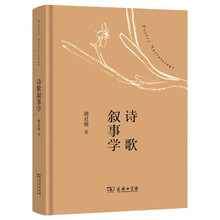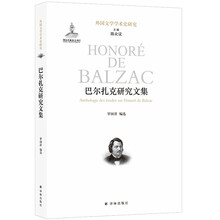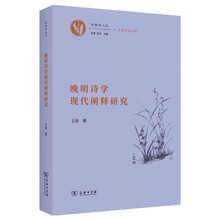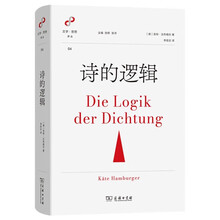《从“惘然”到“惆怅”》一文讨论的篇章,主要表现当前的“我”与记忆中的“我”于不同时间领域的经验世界如何交错纠结。这种今昔对照、“惘然”与“惆怅”往复回环的旋律,并没有在其他篇章中隐没,只是施蛰存要探索的经验世界不仅限于此,这种旋律有时退作背景,以衬托其他的主题前景。例如《桃园》一篇也有回忆感旧的部分,但其中的主题和《闵行秋日纪事》一样,都以知识分子如何被自己身陷的经验世界所制约,在面对书典以外的世界时作出种种反应为描写对象。<br> <br> 《上元灯》里许多篇章的开首部分都处理得非常精彩。譬如《扇》就巧妙地将小说耍展示的世界引入一个储存时间的抽屉之中①。《桃园》一篇则以“忘记”与“不典”的关系作引子。篇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在向外乡人夸耀故乡松江上的土宜时,只能举出“四腮鲈”,而不是“黄桃”,因为“松江之鲈,毕竟是靠了苏东坡游了一趟而出名的”,而黄桃却因为“不典”而理应被人遗忘(第42页)。由“不典”而“忘记”正好说明知识分子意识世界的畛划。知识分子被“典”所支配,被他所能接触的文本世界所限制;书典以外的世界,只好被他悬置。[因此,“我”“忘记了世界上还有着这种好的德行”(第4:3页)、“忘记了”曾是同窗的桃园主人的“名字”(第45页)。]直至因偶然巧合,或者在未能幸免的境况下,置身于陌生的“不典”世界时,就会试图以原有的认知能力去消解当前的困惑。这在《闵行秋日纪事》一篇最为清楚。<br> <br> 《闵行耿日纪事》以传统典雅的悲秋情怀开始①;于时,“我”收到朋友“无畏庵主人”的来信:<br> 小庵秋色初佳,遥想足下屈身尘市,当有吉士之悲,倘能小住一旬,荷叶披披,青芦奕奕,可为足下低唱白石小诗,扑去俗尘五斗也。<br> 无畏(第75页)<br> <br> 这位朋友仿佛只活在书册中。无畏庵是“荷叶”“青芦”伴唱“白石小诗”的世界;里面有的是“收集来的东洋小盆景”,“书斋里的数百种元明精椠书”,“从败落了的旧家”买到的太湖石……(第75页)。盆景、书册都是移根养殖的“典中”世界。对“我”来说,情绪上充溢的是“吉士之悲”,实际生活是“五斗俗尘”。无畏庵主人的邀请,就引领“我”开展了一段旅程:走进信中所宣示的文本世界。<br> 于是他在旅途翻车后看到的是米莱的画幅(第78页)②;到闵行后,他闲着没事,缓步江滨,看到“渔船如落叶似的在荡漾着”(第81页),此地“静寂得如在中世纪神话里所讲到的有怪异的船只浮到仙境里去的江流”(第8l页)③;在小巷徘徊企候他曾遇上的美貌女子时,“他不禁想起从前诗词中所写的门巷愔愔的情景”(第85页)。这种认知的方法和态度,正同于议论故乡会想起《赤壁赋》的“松江之鲈”,也同于《上元灯》篇中“我”想起的“珠箔飘灯独自归”(第18页),甚或《扇》中的“轻罗小扇扑流萤”(第8页)。“我”的经验意识已被“典中的”文本世界垄断,外在的现实世界只会被文本世界吸纳融化。“我”在往闵行的旅程中遇上了“盐枭”的女儿,一个“贩鸦片吗啡的人”,可是“我”没有因此身陷“黑暗的”、“丑陋的”罪恶世界;反之,他看到的是“雕刻在月光里”的她(第82页),听到的是“在朦胧江水上响起来的”笑声和歌声(第87、85页)。最后他更内疚自责,说自己“无端地惊散了…群平安的过浪漫生活的人”(第88页)。由此看来,所谓“闵行秋日纪事”,只是一次由文本到文本的活动而已。无畏君在篇中的形象和行动并不突出,然而他的“精刻本书”和“翻检名家藏书志、书目,研究纸质和字型”的行动,实在是本篇故事的指涉(referent)所在。正因如此,在篇中无畏君不能解释那神秘女子的情事,只有他的仆人——一个可以摆脱文本限囿的人,才“知道事情的真相”(第88页),可这“真相”传到“我”的耳中,又转化成一个浪漫传奇了。<br> 与《闵行秋日纪事》中的“我”相比,《桃园》的“我”较有自觉反思的能力;他会为自己过去托辞不到鞋匠儿子家里玩而感到“疚心”(第45页),他又具有“天赋的一种感伤的情绪”,早岁曾为卢世贻(后来的桃园主人)失学而“暗暗地哭了几次”(第46页),更鄙视那些嘲弄卢世贻的“出身富贵之家的同学”(第45页)。然而,这一切其实都可以归于知识分子所以自慰的、浅薄的人道丰义。<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