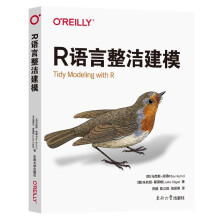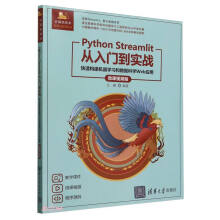2.作为“同盟者”的百年之痒
作为中国文学的一种现代意识形态,“文学决定论”对后来文学总体样态的影响,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推动了文学和政治的结盟。长期以来,学术界在清理这个话题时,过多强调的是政治作为强势话语对文学的吸附和文学的被动性。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结盟,从正面来看,表明的是政治对文学的征用,但从反面来看,显现出的却是社会价值层面上文学对政治力量的借用。就五四新文学发生期文学具有的历史属性和文化品质而言,可以这么说,即便没有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学政治化与革命文学的大力鼓吹与推进,没有创造社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后来的急遽转向,文学走向政治,或者说中国文学史从“文学革命”过渡到“革命文学”都是不可避免的——原因很简单,“文学决定论”的思想动力学使然。
倒不是说强调文学的非常功用就必然导致文学走向政治,而是说“决定论”这个现代最大的文学乌托邦,会给文学走向政治铺设相当自然的通道。因为不管我们怎么理解文学,不可否认的是,文学说到底其实就是文学;就像音乐和美术无法承担家国天下的重任一样,文学同样与国家兴衰无涉。然而在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知识分子的价值预设中,文学已然被假定地赋予过度沉重的历史使命和社会功能,承受着不可承受之重。在文学无法完成这种自我假设的价值使命的时候,借力或者说寻求同盟便是最好的方式。这个时候,有着相同的历史目标、具有更强势力量的“政治”的出场,无疑为文学提供最理想的合作伙伴。于是,文学和政治的虚假的同一性出现了。在郭沫若的眼里,“艺术家以他的作品来宣传革命,也就和革命家拿一个炸弹去实行革命是一样”,因此他号召青年去“做自己艺术的殉教者,同时也正是人类社会的改造者”。即便是在创作上强调“主观”、“抒情”和自我叙写的郁达夫,也主张“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号召“世界上受苦的无产阶级,在文学上社会上被压迫的同志”团结起来,共同战斗。
早期的中国文学知识分子,牢牢把自己的文学梦想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即便鲁迅也不例外,认为“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事实很清楚,这边厢文学想借政治的平衡木完成自己的直体后手翻,那边厢政治却要在文学的鞍马上完成它的托马斯全旋。只是文学和政治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力量,如何维持文学和政治的平衡,既实现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又保证文学自身的自足性,实现文学和政治的双赢,这在当时许多作家那里是个相当有难度的问题。尽管在二三十年代不乏类似的讨论,但所有的讨论最后似乎都被置换为艺术与政治的话语权力之争,因而变得针锋相对和不容置疑起来。于是,文学和政治虚假的同一性解体了。文学和政治的相互借力变成政治的单边行动。因为,文学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借力,往往是以自身的角逐力为基础的,文学和政治两种力量的相互借力,从一开始就是在不对等的情况下展开的;如果说开始时,文学还有借力的意识,那么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以及后来文学界对“新月派”、“人性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等的清扫和批判,文学只有被借出而没有借人的份,从而被彻底卷进政治的强势话语里难以自拔。清醒如鲁迅者也矛盾重重地说出“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的”,却承认文艺“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这样的话。从左翼时期瞿秋白申明文艺“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到延安时代毛泽东宣布“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而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由此往后看,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只见文学鞍马上漂亮的政治托马斯全旋,徒不见政治平衡木上优雅的文学盲体后手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