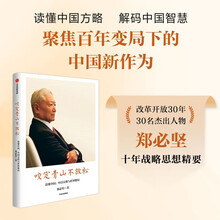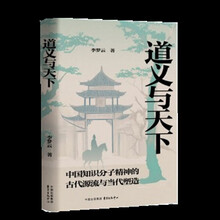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帝王要守礼无疑是事实,而礼是法的一部分,故守礼就是守法。
春秋战国之际,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提出“以法为本”,主张“君臣上下贵贱皆依法”。强调“刑无等级”,厉行“刑上大夫”,确立了地主阶级的法治原则。乃至汉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儒学为一尊”的基础之上,推动了礼与刑的融合过程,具体讲,就是把儒家的礼仪规范纳人法律令,确立了礼法合流、德刑并用的法律原则。
礼法合流,使得中国古老的“王要守法”原则和新兴地主阶级所倡导的“刑无等级”原则,在封建法律制度中被继续存留下来。据《汉书·张释之传》记载:有一次,文帝“行出中渭桥”,有人惊了御马。廷尉张释之据律判处罚金,文帝认为处罚太轻。但张释之坚持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公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文帝也就承认“廷尉当是”。
这种认为皇帝应和天下人一样,共同遵守法律的言论,不绝于史籍。东汉张敏说 “王者从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晋刘颂也强调:“人君所与天下共公者,法也。”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不仅学者及官员主张人君应与天下人共同守法,许多皇帝,如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等,亦有此类言行。
据《隋书·文四子传》记载:隋文帝的儿子杨俊在任并州总管期间,横行不法,“民吏苦之”,文帝杨坚依法惩处了他。当仆射杨素请求文帝宽恕杨俊时,文帝愤然说:“我是五儿之父,非兆民之父,若出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以周公为人,尚诛管、蔡,我诚不及周公远矣,安能亏法乎。”这实则主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又据《贞观政要·公平》记载,李世民针对长孙无忌犯法请求宽免一事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耶?”表示皇帝自己也要守法,无权任意变通更改“天下之法”。
但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是,王应守法这在中国古代还只是停留在观念上、理论上,而没有将其制度化、法律化,以至于在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王之守法与否,完全取决于帝王个人的品质修养或政治形势是否需要。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专横,所以各朝各代都曾发生王权与法律的尖锐冲突,并在这种_冲突中,塑造了张释之、魏徵、戴胄、包拯、海瑞等执法如山,敢抗君命的“清官”形象,也塑造了秦始皇、隋炀帝、朱元璋等任性的“暴君”典范。值得庆幸的是,王应守法的观念并没有在这种冲突中被淹没,几千年来广大民众对“清官”和“暴君”的始终如一的褒贬爱憎,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文化传统最深厚的积淀层是在民众之中。
中国古代的平等观,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新兴地主阶级反对以维护宗法等级特权为内容、以秘密专横为特征的奴隶制法律制度的斗争之中。
奴隶制法,是维护宗法等级特权制度的工具。夏、商、周三代的法律,除确认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级的对抗这一基本事实外,又在此基础上把人划分成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五等。“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这就是所谓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从法律上确认不同的等级,其身份地位、权利义务各不相同,甚至礼节仪式、服饰器用都要严格区别,不能僭越,充分体现了“礼有差等”的特征。
另外,奴隶制法“是这种专门为有特权的少数人所知道的法律”。奴隶主贵族顽固恪守“临事制刑,不预设法”的秘密法准则,因为他们确信,只有“法不可知”,才能收到“威不可测”的效果,不知道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什么罪处什么刑的人们,自然会“常怀怖惧”。同时奴隶主贵族对法律知识的垄断和独占,便于其随心所欲地庇护同族,打击政治异己力量,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诚如梅因所言“他们对于法律知识的独占,有力地阻碍了当时在西方世界开始逐渐普遍的那些平民运动获得成功”。
在春秋时代的中后期,作为特权等级制度的被压迫者和秘密专横的司法制度的受害者——新兴地主阶级,为了争取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权的权利,抵制奴隶主贵族的司法专横和经济掠夺,便把斗争矛头首先指向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核心、以秘密专横为基本特征的奴隶制法律制度,并在这一斗争中,历史地高扬起了平等的旗帜。
特权等级制度是秘密法赖以存在的基础,秘密法又是维护特权等级制度的最佳形式,二者相辅相成,而平等则是摧毁特权等级制度的唯一有效的理论武器。新兴地主阶级主张“布之于公”、“事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依法”。要求法之于人,犹度量衡器之于物,不允许有高低贵贱之别。商鞅则更明确主张“刑无等级”,即,“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命,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不为亏法,有善于后不为损刑,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法律平等观的提出,是古代法制史中最辉煌的一页,它不仅摧毁了一种旧的法律制度,而且开辟了古代法律制度发展史的新时代,为古代法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我们将古代东西方平等观产生、发展、演变的不同历史环境和过程加以比较,或许将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深处,把握和理解近代东西方宪政制度存在的种种差异。
在中国,秘密法阶段从公元前21世纪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36年,长达15个世纪之久,贯通了整个奴隶制社会,这在世界法律发展史上是罕见的,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秘密法阶段不过两三个世纪,并且都是在“共和政治史的初级阶段,就获得了一个法典”。出现这种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存在一个人口众多、人身自由、经济实力雄厚且自备武装的特殊的平民阶层。平民实力的增长和坚持不懈的斗争,大大缩短了由不成文法时代向成文法时代过渡的历史进程。在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平民阶层自始至终都没有形成独立的,足以和奴隶主贵族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起不到西方平民那样的催化作用。所以,由不成文法时代向成文法时代的过渡,也就显得缓慢而又漫长。
公布成文法,这一在西方通过平民的斗争而完成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则由于平民阶层的软弱,不得不依靠后起的,主张“事断于法”的新兴地主阶级来完成。由于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封建制,所以,通过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而公布的成文法,实质上标志着一场革命,即奴隶制法律制度的瓦解和封建制法律制度的形成。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平民阶层不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所以通过平民的斗争所公布的成文法,只能是对奴隶制法律制度的改良,它不仅没有导致奴隶制法律制度的崩溃,相反却迎来了古代西方奴隶制法律制度繁荣时期的曙光。
无论是中国的新兴地主阶级,还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平民阶层,作为秘密法的受害者,在反对奴隶主贵族的传统特权和司法专横、要求公布成文法的斗争中,都高扬起了平等的旗帜。罗马的平民保民官该犹司.德伦几留司·哈尔措在谴责贵族的骄横气焰时说:“既没有什么可以限制他们的凶横,他们便可以用所有法律的威吓与惩罚来摆布平民了。”所以他主张:“任何高悬在人民头上的法律,都得是他们自己给予执政官的,这些而且只有这些,才是他们可以引用的,绝不允许他们把自己的放肆和任性当作法。”当《十二铜表法》正式颁布时,十人团宣告说:“尽十个人的智力和远见之所能及,他们终于为大家制定了平等的、上下一体沾惠的法律,……罗马未来的法律应该做到大家一致满意。”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