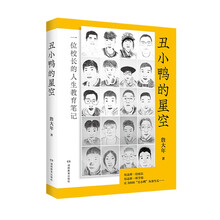在《大学人文教育的理念、目标与模式》①一文中,甘阳先生挑明,“中国大学目前的学美国,实际只是在学其皮毛,而未学到其根本。”(12页)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大学“几乎从来没有问过,美国大学的根在什么地方”?换言之,搞不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的仿效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生命力,遑论因地制宜、随机应变。那么,美国大学的生命力植根于何处?在甘阳先生看来,美国大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其“自觉地植根于西方文明的深处”(12页)。这一“文明自觉”,乃两次世界大战以铁与火的政治紧迫性镌刻在美国通识教育机体上的醒目徽标。换句话说,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体制在其建立之初,即与其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自觉”或者说“灾难性的现代处境”紧密相关。
一般认为,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起点在于1917-1919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当时,“一战”的硝烟正笼罩在欧洲大陆上空。最初,好多美国人想不明白,作为新大陆的美国为什么要卷入腐朽的旧欧洲的战事?这不是没道理的追问,因为美国政府对民众的教化向来以“新”作为着力强调的教育品质——“新大陆”、“新工具”、“新技术”、“新世界”……换言之,战前的美国自觉站在“新”的一边,敌视、反对、抛弃“旧”的一切,而战争教育了美国。美国联邦政府痛感有必要对美国公民进行西方文明史教育,要他们明白作为新大陆的美国与古老的欧洲文明的关系,由此表明美国参战的必要性(18页)。由此可见,是美国的政治家而非教育家首先意识到,抛弃欧洲古老文明的传统,单凭追新骛奇,不可能建立起美国自身稳靠的文明根基与底气,于是始在大学中开展“战争教育”。正是在此背景上,哥伦比亚大学把以“战争问题”为主的公民教育课程改造为“西方文明”课程,进一步强化“新”一“旧”世界的内在关联,为美国通识教育体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如果说“一战”让美国人清楚意识到自身与欧洲古老文明的关系,那么“二战”则引发了美国人普遍的“西方文明危机感”。日后影响深远的“哈佛红皮书”(原名《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就是在战争最激烈的岁月中被反复讨论、修订并发表的。美国的教育家为什么要在战争最激烈的岁月每星期聚会一次频繁讨论“通识教育”问题?教育问题比战争现实更紧迫?作为“红皮书”的担纲者,哈佛大学校长科南指出,“无论在信息时代可以获取多少信息,无论在技术时代发展多少专业技术,无论数学物理生物科学如何发达,无论可以掌握多少外国语言,所有这些都加起来仍然不足以提供一个真正充分的教育基础”(18页),因为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仍然没有触及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美国)的文化模式”,或什么是在古老的“传统中形成的智慧”(19页)。在美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看来,教育问题比原子弹更重要,不仅因为原子弹归根结底要由人来掌控(回想政治科学大家罗尔斯反省日本核爆五十周年的痛彻文字),更因为教育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品格与未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