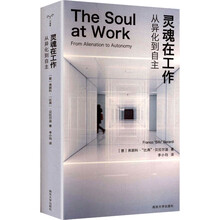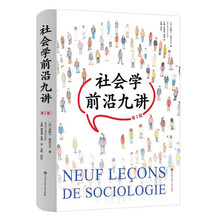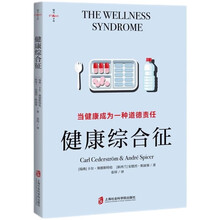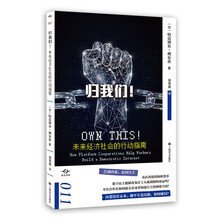涂尔干理解在没有角色分化的原始社会和角色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之间存在社会归属的差异。在封建社会中,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名农夫,而社会归属也就是认同的基础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农夫们的生活以及生计是共享的。在有着精细劳动分工的复杂社会中,个人认同是与其他人的职业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对他们中许多的成员素昧平生。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83)后来就把现代民族国家称作“想象的共同体”,它包含了那些从未碰面但彼此认同的人们。
涂尔干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身份不仅由宗教联系和民族形成,而且日渐由职业来形成。经理和工人、专家和官僚都根据职业脚本来行动的。涂尔干证明了在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日益精细的经济惯例。他表明,职业网络正在变成经济惯例与意义的根源,而后者被韦伯视为现代经济行为之核心。劳动分工创造了一个与职业网络重叠的复杂罗网,每一个网络都有传输特定工作习俗的精巧社会化过程。
网络如何约束经济行为
很久以来社会学家一直对人们为什么依据经济惯例来行动感兴趣。从韦伯以降的制度主义者认为,那些被社会地定义为自利的习俗是不难解释的。在理性化社会中,人们相信应该自利的行为,并且总是寻求自利行为的新方式。社会地定义为利他的经济习俗则较难解释,但是网络理论家主张,由于我们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所以我们才会遵循利他习俗。我们的名誉、声望和未来买卖的能力,都取决于我们在同侪网络中的行为。
第9章是格兰诺维特的博才大作《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它在1985年给予了新经济社会学一个理论上的极大振奋,他挑战了两个关于经济行为的极端观点,并提出了一个涂尔干主义的中间立场。社会学关于经济行为的过度社会化理念(Wrong,1961)认为,我们遵从规范,就像旅鼠跟随群体一样。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行为的低度社会化理论则似乎认为,个体是原子化的决策机器,并不受文化和社会化的影响。
格兰诺维特认为,个体的经济选择是嵌入在社会环境之中的。工作场所和职业网络形塑了行为,决定了人们可以想象的经济行为的种类,并限制了他们可以从事的经济行为的种类。由此他解释了理性的行动者如何能够决定遵守经济惯例,即使这样做要他们付出成本。
为了说明这一点,格兰诺维特举出了来自制度经济学的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交易成本”理论,这个理论阐述了那些鼓励公司和它的供应商合并,而不是用公开市场去取得供应的情况。威廉姆森认为,当这样做有效率的时候,企业就会同它的供应商合并(“纵向整合”);尤其是在供应商有机会进行价格欺诈的地方。格兰诺维特则证明供应商一般遵循反对价格欺诈的规范,因为他们的名誉和身份依赖于这个惯例。此外,网络也常通过剥夺业务资格来惩罚价格欺诈。因此,企业不需要去收购有机会搞价格欺诈的供应商,因为社会网络会阻止价格欺诈。
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融合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观点中的成分,即人们在收入上是自利的最大化者以及社会学的观点,即社会背景环境形塑行为。比如,在他的模型中,对于买者而言遵循定价的社会规范在长期来看可能是理性的,即使从短期来看这些规范可能妨碍其盈利。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畅销书《信任:社会的美德和财富的创造》(1995)就是建基于格兰诺维特的观点之上,认为对社会网络的信任赋予一个社会以经济优势,因为它避免了广泛的管控,创造出自发的合作与协助,并使得经济关系更具协作性而非律法性。
网络如何生产社会资本并强化惯例
格兰诺维特认为,人们的社会网络可以制约他们去遵守经济惯例,比如反对价格欺诈。第10章是波蒂斯和森森布伦纳的<嵌入性与移民:经济行动的社会决定因素“,建基于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观点与”社会资本“观点之上。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社会网络为达成经济目标提供了一种”资本“。社会学界的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1990)和政治学界的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1993)也赞成这一观点。像格兰诺维特一样,波蒂斯和森森布伦纳表明社会网络可以促进服务于共同体社区的经济惯例,即使这些惯例并不用于狭义构成的个体利益。像格兰诺维特一样,他们挑战了认为人们是在隔离状态下做出经济决策的观点,并证明了惯例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因为网络预期其成员去遵守它们。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