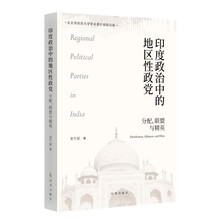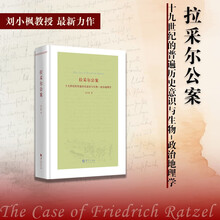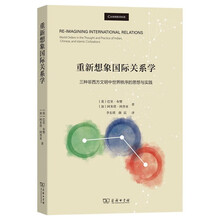如上文所分析,在不存在暴力垄断和宪法法律体系的情况下,安全同样是一种个体生存和繁衍必要的资源。安全为国家行为体带来的生与死的效用。如沃尔兹在其理论中提到,一种新的、高效率的行为模式一旦产生就会导致其他国家的学习。在这种意义下,仅就数学本质而言,镶嵌在已有规范中的选择行为尽管在信息和计算能力有限的语境下是一种高效率的选择模式,然而在一个国际体系紧密联系,国家之间竞争白热化的语境下,则相对于更加高效,更加接近“完美理性”的行为模式而言,则是一种较低效率的“非理性”行为,竞争的需求和既有的制度的供给之间将因此失去均衡,对于制度的边际调整则因此能够带来收益,从而产生了制度变迁的动力。中国近代的改革则是这方面的一个最好的例证。中国几千年形成的森严的官僚等级制社会政治结构由于缺乏科学和必要的权力制约机制而极易滋生贪腐行为,几千年来,中国人对这种政治制度结构和文化带来的恶果习以为常,并不觉得存在不妥,与封建农耕经济相配套的这种政治体制能自我延续而被中国人所长期接受,处于一种封闭的均衡状态。西方世界的崛起改变了这种局面。尽管同样在经济社会学的信徒看来是一种“理性行为”,然而这种贪腐行为严重腐蚀国家和社会的机体,削弱国家的竞争能力。赢弱的民族在西方军事和文化咄咄逼人的侵入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在西方和东方侵略者的压力下,已有的政治制度的均衡被打破,开始了制度变迁的过程,民主和共和的观念改变了这个民族的面貌,使其变得在许多方面与西方传统民主共和国家越来越相似。
总之,如果让历史与理性握手,我们就可以得到较为综合性的结论。即,追求各种物质和非物质的稀缺资源是行为体的终极性追求,然而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并不存在完美意义的最优解,因此国际政治行为体获取最大效用的理性选择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一定历史时期的客观条件基础上的“试错”过程,一旦一种行为模式或者多边资源分配安排被证明具有较大的效用,则这种习惯性资源取得机制就将获得“自我强化”。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