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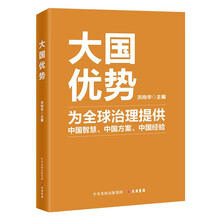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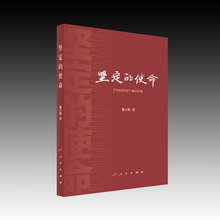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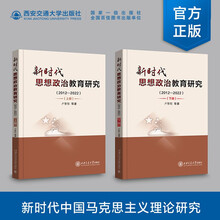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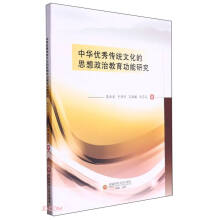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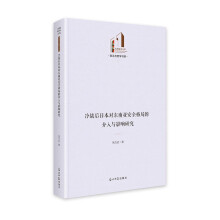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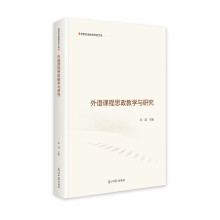

《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视角独特,在近几年中国大陆出版的民国/辛亥题材书中,这恐怕是唯一的一部从辛亥“失败者”的角度、深入探讨“清遗民”们的政治/文化活动,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现代中国的著作。
作者注重“内部分析”的方法,以“同情之理解”的立场来解释人物的行为动机,而不是轻易地下结论,使用是非、进步落后之类先定的概念去裁断人物。这正是严谨的史家的工作。
台湾中研院副院长、前史语所所长王汎森先生专门作序推荐。
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中国人亦由臣民转向国民。然而,有一些著名或不那么著名的人物,选择了同情以至效忠清室的政治立场,后曾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郑孝胥甚至在日记中称“民国乃敌国也”。如何解释和理解这些人物的行为及动机?这一群体的政治立场,是“落后”或“反动”的吗?而且,过去的历史研究,常常瞩目于政治秩序解体后新的知识分子如何来寻求文化的意义与认同,忽略了传统脉络的影响。《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条分缕析,探幽抉微,透过“清遗民”们在民国后的活动和仪式、个人/集体的著作书写、政治主张和思想,以及在舆论视野中的形象及变化,探讨其行为与背后的动机,重新审视这样一群曾被“脸谱化”、“污名化”的人物,并希望借此重新理解近代中国由传统进入现代、从王朝专制迈向民族国家的历程,以及驱动此转变的内在动力。
第七章 王道乐土:情感的抵制和参与“满洲国”
第二节 国家和朝廷的两难
无论支持与否,满洲建国让清遗民产生效忠国家和朝廷的两难。以效忠朝廷的观点而论,完成中兴恢复清室大业,固为许多遗民长期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可是要支持并建立如此国度,必须付出代价,倚赖且听从日本武力的支配。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他们究竟怎样平复个中的矛盾和冲突?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复辟契机
根据庄士敦庄士敦供称,溥仪溥仪离开紫禁城之前数年,曾透过多方管道接触外国人士。这些平日的拜谒来往,与其说为了达成某种政治目的,不如说是替清室制造舆论,寻求外援而发。也正因为如此,逊国后的清室得以开启与日本的外交。就在1923年的秋天,东京发生大地震,伤亡惨重,举世震惊。当时担任清帝师傅的陈宝琛陈宝琛,经由早年在东文学社结识的日人池部政次得讯,从旁鼓动溥仪溥仪,公开任命赴日使节,并致电天皇,表达慰问、助赈之意。此举让原来双方早已断绝的交谊重新恢复,据溥仪溥仪后来自承,目的其实想运用社会舆论,展现“皇恩浩荡”,藉以博取国人注意和同情。尽管不久后清室被驱出皇宫,却因此埋下日后满洲国成立的命运。
历史发展经常出乎人们意料。当中国境内处心积虑想铲除像溥仪溥仪这类的眼中钉时,没料到反而推波助澜,帮助他人实现了政治野心。清帝被迫离开紫禁城,找上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芳泽谦吉(1874—1965)协助逃亡天津,结果愈发使得与他关系日渐密切的日本,意欲利用这颗棋子,达成建立“满蒙王国”的构想。至少从1926年初,有关言论已相继展开。譬如,结合了日本官员、学者及政党要人的“东亚同志会”,便力促迎接溥仪溥仪至满洲。在建设满蒙国度的想法中,该会还声明“中国既不能行立宪政治,则惟有贤人政治之一法”。嗣后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伐”节节胜利,日本田中义一(1864—1929)内阁有意迎接溥仪溥仪东渡,因部分遗民劝阻而未成行。1931年,因为日方对张学良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不满,颇有“迎驾还乡”的传言,隐然为清室的复辟铺起道路。
“九一八”事变发生,是满洲国成立最关键的因素。许多人关切东北问题和前途,就连溥仪与清遗民亦无例外;事变发生未久,也引发了天津的“小朝廷”几许不安。胡嗣瑗在日记接连几天记载此事的发展,特别是溥仪溥仪传谕诸位遗民商议因应办法的情形。从这份已经出版的《直庐日记》手稿可知,参与讨论的陈宝琛、朱益藩、郑孝胥、陈曾寿等人,除了提出审度情势、伺机而动外,并无具体的肆应方案。更应留心的是朱益藩和胡嗣瑗尝表达相异的意见。根据日记所载,朱氏主张对日本应秉持“主拒不主迎”的态度,但胡氏认为此一态度“太固执”了。胡的看法认为,要先看日军和赤俄在东北势力的变化,然后再决定溥仪溥仪的行止;至于在此之前,应尽量少露痕迹,避免外界的舆论及浮言,引起惊动。
《直庐日记》纪录遗民互动的情形,说明清室内部对“九一八”事变有几种不同意见:第一,事件陡然发生,刚开始时清室并未立即决定投靠日本;相反地,遗民感到意外,态度彷徨犹疑,显得不知所措。第二,主张拒绝接受日本扶持的朱益藩,尽管无从得知其想法到底如何,但充分代表部分遗民反日的情绪与立场。第三,胡嗣瑗的说法必须给予重视,代表另外一股遗民们的意见。以事后发展的结果而言,走上建立满洲国之途,其实与胡嗣瑗的选择颇有密切关连。
遗民对建立满洲政权的态度
溥仪后来酝酿复辟、建立满洲国,许多清遗民固然称喜,但也有人表示不同意。细究其因,认定此一计划将受日本左右,无法自立自主。以接近“小朝廷”的遗民来说,陈宝琛便以为不应贸然行事。他给家信中提到:“旧臣遗耈,或以天下嗷嗷为机会,我则虑其一片烂泥之无从着手,且环顾亦未得其人,则仍是为人所利用,徒自蹈危机也。”陈的态度,引来其他遗臣非议,有人甚至以怯懦见疑。后来事果成行,陈氏端居深叹,直到临终之前,仍感负疚君主。另一位身处北京的章钰,给胡嗣瑗唱和的诗中,传达相当悲观的语气,如谓:
东风消息问天涯,一朵红云艳莫加。
安稳仍栖同命鸟,高华自压隔墙花。
忍言冰雪前番劫,信是神仙到处家。
照海倚云知有待,漫愁国色溷尘沙。
章氏诗集出版之时是1937年,而该诗撰于旅居天津期间,地点系溥仪溥仪住过的“张园”(即张彪旧宅)。若非睹物思人,相信绝无诗中内容。“东风消息”意指溥仪前往东北一事;至于“高华自压隔墙花”,显示深信满洲政权终将为日方欺压,难以自主,故章钰感到不安而“漫愁国色”。
有的忠清遗民还坚信,原本中兴清室的大业,可能因满洲国成立,将使“忠君”的态度加速“污名化”,不见得符合民心期望。铁良和袁大化(1851—1935)即共同反对溥仪赴往东北立国,指称此举“恐失人心”,又言:“人心所向,即天意所归,可不谓知所本欤?”在部分遗民的心目中,恢复清室与建立满洲国,两者意义也有距离,不必然等同视之。因为前者乃世受“国恩”,攸关个人的声名气节,属于“不卖主”;但后者涉及国家立场,视如“卖国”行为,会引来强烈反感。最具体实例乃1932年6月27日,当时满洲国已成立三月之久,《申报》上有金梁鬻卖笔墨的启事,颇能解释当中区别:
金息侯先生梁,自去秋沈变即携眷避津,鬻文为活,不问人事,既未卖国,亦不卖主,主身自有本末,不辨自明。
尽管后来金氏仍然远赴东北,任职奉天博物馆馆长,欣喜溥仪就任满洲国皇帝,但此则启事至少显现他最初时犹疑的心情。据称吴郁生“临终遗命,敛以常服,留冠去顶戴,以示己为清朝负罪之臣;且属如民国或满洲【国】有所赠恤,皆不许受,盖非出于清朝也。殁后汪兆铭汪兆铭派青岛市长往祭,溥仪亦遣人往祭,并予谥文恭。其孤谨遵先志,咸坚拒却”。从吴的“遗命”来看,系以遗民自期;然而对自己死后安排,却无意接受民国和满洲国满洲国,认定两者均不能代表一己心志,由此推断反对满洲政权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