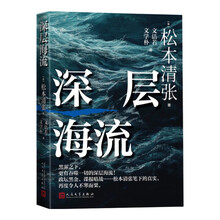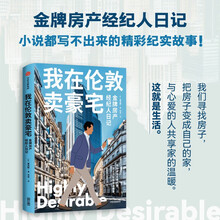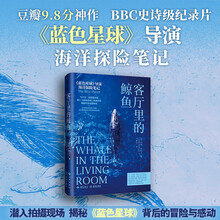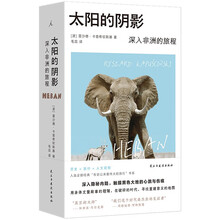永久的悔与无尽的念
郭齐勇
我很快就要由不惑之年跨入知命之年了,回首知青生涯,总免不了思绪万千,浮想联翩。我们这一代人有不同于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和生命情调,有特殊的遭遇、坎坷、困惑与痛苦,有异代人难以理解的喜怒哀乐。我们属于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一代,我们曾经盲目地然而却是真诚地拥有为理想、为国家、为他人英勇献身的精神,并付诸了实践。
反思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一方面多少有些留恋那稚嫩的莽撞的苦斗,那蹉跎岁月的青春、热血和汗水的无私奉献,以及第二故乡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思想蒙昧和“文革”氛围重压下的精神自戕、自我萎缩而汗颜,为自己后来经历了思想解放,并逐步摆脱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觉悟到知识分子的自立之道和生命自我的飞腾超越而暗自庆幸。
原罪与救赎
我们生活在没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社会,实际上很难体验西方人的原罪感及其意义。我这里所说的“原罪”,是极左年代的所谓阶级原罪,即笼罩在所谓“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尤其是知识分子头上的无形的紧箍咒——罪感意识,生而有罪的意识,父债子还的意识,低人一等的意识。
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远远早于“文革”。即使不谈1949年以前的革命中的类似行为,至少可推至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前期。所有这些都是与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自我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我个人早在“文革”以前,在1964年读高一和1965年读高二时,就已向学校提出过不再念书而奔赴农村或边疆务农的要求。记得汪子英校长、刘克刚主任(教务)专门与我谈过话,劝我打消此念,认真读书。我当时十分欣赏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前驱者,决心以他们为榜样。然而在下意识里,这种要求却是与自己的tt出身不好”有关系的。当时的一种内在痛苦,是渴望参加革命而因所谓“出身”问题和“海外关系”问题而不得参加革命的痛苦。这种阿Q的苦恼在我们班上(省重点学校的重点班,同学们多数是高等院校教职员工子女或城市工商业者的后代)特别突出。
1966年6月5日晚,我与班上最具革命敏感性的同学们,受北大、武大“文革”巨变的鼓动,给校党总支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强烈要求立即停止高三毕业班的备考复习而积极投身火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次日形成了全校学生以请愿和大字报为主要形式的“六。六”运动。省市迅速派出了以一位资深的团省委副书记为首的工作组处理此事。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与冯达美、孙俊3人被工作组和党总支内定为“三家村”小反革命集团。
我们当时无疑是激进的左派,是毛泽东的十分幼稚且狂热的信徒。然而由于我们必须承受由父母带来的“出身罪”,而不得参与“革命”。因此,我们“革命”的动机首先为当局所怀疑,且视为异己分子,随之而起的以“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不仅把我们排除在外,而且把我们(所谓“黑五类”)也作为斗争或准专政对象。历史往往无情地嘲弄历史的参与者,我们这些“先知先觉”的造反者很快被“后知后觉”的造反者所抛弃。历史的旋涡总是使中心滚进边缘,而边缘人物每每占据中心。
现在看来,十分可悲的是,我个人在这种局势下陷入到严重的精神自戕、肉体自虐的境况之中,陷入了偿还原罪的苦闷和折磨之中。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之深,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而我们这种救赎之道,只能是自责、自虐,以及奴性十足地服从强大的他在力量的安排。尤其不能原谅的是,我竭力表白自己积极参加革命、接受改造,并努力自我改造,以至“脱胎换骨”的决心。例如,我曾经主动地天天打着赤脚到开水房为好几栋教学楼打开水;我这个连任几届的班主席(班长)给我们班的几任班主任老师刘乐芳先生、张丽华先生等写过大字报,揭发他们给青年学生推荐修养之类的“毒草”;我积极参加当局领导的批斗活动,特别是对许简老师《三言两语》的批判,记得我曾把许老师的写作背景与反修斗争联系起来,查阅报刊,上纲上线,写大字报说他抵制反修;我曾经追随红卫兵到珞珈山的几位同学(他们的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家里去“扫四旧”,在唐小蓓同学家还高声指责她父亲唐炳亮教授,大约是声讨他这个已摘帽的“右派”分子的罪行;1966年暑假我在家中收到班上红卫兵的一封勒令信,让我集合祖父母、父母亲等全家人高呼“老子反动儿混蛋”等十几条口号,每条连呼几遍,我照办了,虽然痛苦至极,仍然造祖父母、父母亲、叔父母的反,勒令他们扫街,佩戴自辱的黑符号……在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我们这些“黑五类”也逐渐“咸与革命”了,我们参加的“红十月战斗队”,虽然是比较文雅的,但也做过蠢事。我记得我与几位同学在某年的大年除夕,还跑到“走资派”邓铁生书记家狠狠训斥了他一通。
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也许放在特定的“文革”环境中算不得什么。但“文革”过后,痛定思痛,深感当年在“左”的氛围中,自己的所思所言、所作所为,是何等地“左”,何等地有违人性啊!或许恰好因为自己有“黑五类”这顶帽子的限制,才没有走得更远。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激进主义的熏陶下长大的,虽然在“文革”中,我对滥杀滥打无辜,“打砸抢抄抓”的无法无天状态深感恐惧,对给我们的师长的种种侮辱(如我校红卫兵给著名的女教师、化学权威张J睢聪剃阴阳头及给一些老教师戴高帽批斗等)和杀伐(如我校著名数学教师陈邦鉴先生自杀等)深觉不公和不平,然总是以所谓革命的逻辑来说服自己,以毛泽东赞扬湖南农民运动14件大事的态度来对待所谓的“群众运动”。在这种麻醉剂下,我认同了街道一些不三不四的“群众”数度抄我自己的家,同时也竭力与家庭、尊长与“反动学术权威”的师长划清界限。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