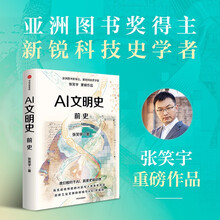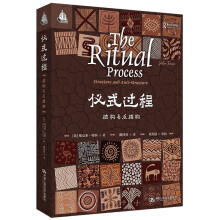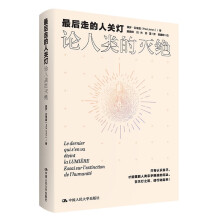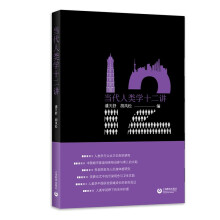另一个部分,我想跟中心-边缘区域的相对化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它在所有的区域研究提出了一个多元性视角。这个多元性表现在空间上,也表现在时间上,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空间上的多元性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费老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将中华民族聚居区划为六大板块、三大走廊的格局,这六大板块、三大走廊就是一个空间很清楚的区域,所以它的差异性一眼就可以看到,我就不多提了。但是空间结构的差异性跟中国历史叙述之间的关系里面,实际上提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时间结构上的多元性,不仅是一个空间的多元性的问题,虽然事先有一个稳定的中心-边缘叙述,但是他对这一点是有很清晰的认识的。我在这儿把施坚雅的一段话念一下,算做一个结束。他说:“历史盛衰变化的传播,在大区域之间经常是不同步的,区域发展周期不仅关系到经济的繁荣与萧条,也关系到人口的增长与停滞,社会的发展与倒退,组织的扩展与收缩以及社会秩序的和平与混乱。此外,由最底层的集市系统而上,每一层次中的体系均有其独特的运作模式和历史,它可以被视作人类相互作用的时空体系。在此时空体系中,与空间结构上的差异性一样,时间结构上的差异性也显示了一个体系的特征。”<br> 我觉得他提出时间体系上的结构差异性对于中国历史如何叙述是很重要的一点,虽然他讲的是内地经济,只是在经济区上的。他说:“对于有层级结构和地域特点的历史学来说,基本的时间单位是那些内在于一个特定区域体系的周期性的、赋予动态的事件;这种方法与通常的分析法不同,它强调中国历史中区域之间的差异性,而不是使之模糊,无论是笼统的概括或是仅着眼于各不同区域体系的发展的平均水准都会减弱或模糊地域间的差异,从而不利于研究整合唯一的中国历史;相反如果要获得对一个文明历史的整体认识,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它的各组成部分的独特而又相互作用的历史。”我觉得他讲的只是一个经济,不过把它放到民族史和其他的构架下这个问题更突出,因此,所谓的“多元一体”的一体性必须以空间和时间的差异性为前提,否则这个叙述的“一体”就完全是自上而下的自我中心的叙述了。<br> 我觉得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中国历史里面最独特的一点是我们可能最终会牵扯到的,一个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差异下,中国文明在历史中是通过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发展了一个能够不消解这种多样性、但是同时能够使它们在一个大的相对稳定的结构里面存在的可能,这是一个新的政治智慧,我相信在我们这两天的讨论里面,包括我看到的提纲里头,念群的也好,唐晓峰教授的也好,都已经涉及从这个政治文化的角度去理解,怎么把这样的空间和时间的多样性跨度整合在一个政治架构和制度法律这些所有的问题里面。所以,我就不多用时间了,我希望多一点讨论。也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区域”到底是一个概念、方法,还是视野?其实我们在泉州的时候也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这都好像不确定。我个人的一个体会,为什么还是要把这个区域问题提出来,原因恰恰是因为区域这个概念的模糊性、重叠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它有意义,原因是我们无论在经济史的框架下、民族史的框架下,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单一史的框架下来理解的时候,都有一些其自身带来的局限。区域在一定意义上似乎提供了一个新的综合性的视野来理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是某一种的视野,所以我觉得关于具体的区域界定和它的模糊性与重叠性的问题,事实上在过去的历史研究里面也都有一些涉及,我相信我们在这两天的讨论里面也许还会不断地回到这儿来。<br> 以上这些完全是把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我个人觉得还可能有一些意义的,有一些是很早的文件,不是当下的研究,重新带到我们这里来思考。我就提供一个引子,抛砖引玉吧!<br> 王铭铭:现在进入自由讨论的阶段。刚才有一个程序我忘了说,就是简单介绍我们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这个名字读起来比较累,很别扭,但是拿了民族大学的钱,就必须挂着民族学,不能直接叫人类学,但是我们做的是人类学的研究。中心成立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也办了一些讲座,开过多次国际国内的讨论会,办有一个杂志叫《中国人类学评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br> 刚才汪晖讲到了很多人,有好几次涉及施坚雅,我们知道他最近刚过世。他跟费孝通教授是有过交往的,而且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我怀疑是他跟施坚雅见过面之后写出来的,因为施坚雅在很早的时候就开拓的中国区域研究的路径,在国内比较弱。但是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篇文章里面所谈的区域理论完全不同于施坚雅,这个不同之处在于施坚雅的中国地图只有汉族地区,费孝通教授的地图呢,整个延展到古代中华帝国的版图边界上,当然也包括近代以后确定的边界。那么,中美的这两种“中国观”是很值得比较的。国外画中国地图的时候大概会很愿意像施坚雅那样说只是汉族的,那在国内来讲,你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这样一个帝制国家转变成近代民族国家的这个历史后果。我刚才很有感触,北大费孝通讲座曾经委托我给施坚雅写信邀请他来做第二届演讲,但是很遗憾,我的信正好是在他病重的时间到达的,所以没过几天就传来他过世的消息,在此我表示哀悼。<br> 下面就请大家开始自由讨论吧。<br> 潘蛟(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刚才汪教授和王教授都谈到了,实际上区域划分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从行政区域、文化区域,而且对文化我们把它提到哪一层,把文化的同质性提到哪一层,从行政的区域,我们把它追到哪一块,是直接追到税赋下面还是朝贡之外,有很多的可能性。还可以说,今天有经济的、文化的、族群的这种划分,都是交叉的,而且好像在不同的时期,人们认定的区域还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最后好像得还原到那个时期人的那种权力的欲望、权力的关系,这些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今天这种讨论,是不是想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区域划分,或者说更科学的划分?我们具体在追求一种什么东西?我比较好奇这件事情。<br> 龚荫(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刚才讨论的内容非常丰富,从我的体会来说,可以说是茅塞顿开,视野扩大了许多。我经常说,我就是那么两下子:民族政策和土司制度。这次能来参加这样的盛会,我感到很高兴。另外就是,我的《中国土司制度史研究》,180万字的书稿,我想到中央有关部门寻求支持,把它印出来。我做这个花了四五十年的心血,已经有1000多万字的资料,想把这个东西弄出来。前面王教授提到的《中国土司制度》可以说是错误百出,甚至有的人说,我们有几代人都在那里统治,你们怎么不写呢?我说我写的是县一级以上的,你们那个还不“人流”嘛。所以这一次就想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土司制度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加全面。听了刚才的讨论,不管按区域也好,按朝代也好,按时间也好,按空间也好,给我的印象就是方式方法与理论论述的问题,还有宏观与微观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如何看得出哪一种东西,用哪一种方式方法、哪一种理论进行论述?刚才所谈的民族史,我是学民族史的,但是我又是否定民族史的。我记得《民族研究动态》曾经叫我总结近百年来的土司制度研究的情况,我就谈到过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写了那么多套民族史,哪一个少数民族的历史你从三代轮下来就是了,我说三代的时候,这些民族是王朝管不着的荒服,那个时候只有区域划分。秦统一了以后才谈得上民族了。秦统一的时候,北方就是匈奴,他派了一个蒙恬把匈奴撵出河套。汉的时候,匈奴就更加发展了,他在北方建立了一个民族政权,汉朝要全国统一,就开了30万军队去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去了差点回不来。所以说是在古代民族政权建立了以后,中央王朝才意识到它的危机,马上就要把你打散。所以前面的那些民族史,都是有点玄的。我认为谈民族史成功的时候,是在元以后的事情。元以后民族地方的流动、名称、民族的历史位所,基本固定下来,这样民族史在元代以后的叙述逐渐突出。元以前的民族史都是断代的,所谓哪个民族正宗的是从哪一支发展下来的大多不可靠,所以那些民族史学家千方百计研究族源,民族发展史说不清楚的地方太多了,不过这样民族史学家就有事情可干了,去考证什么的。<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