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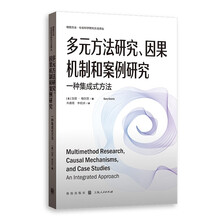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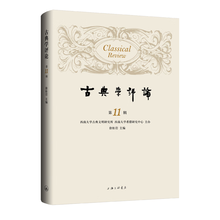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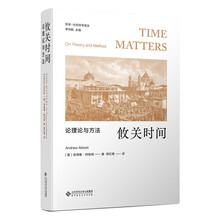

我们及身边的林林总总无时无刻不在揭示——许多中国人能做出任何言行不一的事情,观念和行为始终冲突不断。有“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传统德性标准,却会出现“嘴巴里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口是心非”、“明哲保身”、“人情和面子功夫”、“关系网”等负面现象;我们在其中不解着,痛恶着,失落着。《中国人观念与行为》深入而精到地剖析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对他人和世界的迷茫,在这里会找到一些或浅或深的答案。
儒家传统的意识形态及其所塑造的政治结构、家族制度、社会规范,对汉代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压力——儒家伦理的理想目标与实践范围间的冲突,即观念与行为的冲突。现代中国,这种压力仍根深蒂固,这一冲突表现尤为显著。《中国人观念与行为》秉持这一基本观点,关注了现代中国观念与行为在诸多方面的冲突以及呈现的困境;并通过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去理解这些观念与行为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作者意在引领我们,看看处于现代生活中的中国人,究竟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将来又会朝着什么方向走下去。
摘自第四章《中国人的道德思考》(韦政通):
道德教育的困境
……
很久以来我们的道德教育,总是偏重于通过文字灌输古训(现在还要包括今训),重点多半只教人应当如何,即使切近生活的指点,也只是告诉他何者为宜、何者为不宜,人完全是被动的,好像你只要遵照那些指示去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似的。这种教育的方式,与我们前面提到的恰恰相反,因为它重视的是权威与教条,忽视了道德教育必须要靠个体的自觉与自动做基础。这种教育不免使人遭到“闭门造车,出门难以合辙”的困境,一旦生活上面临必须作抉择时,依然不知所措。
这种教育的方式,John W.Gardner有很生动的描述,他说:“我们常常在应该教导年轻人种植他们自己的幼苗时,却给他们以剪下来的花朵;我们用早期创新的产品来填塞他们的头脑,却未教导他自己去创新;在我们应该把心智视为供我们使用的工具的时候,我们却把它当做要填塞的仓库。”这已足以了解我们一向重视道德教育,而又总是不能产生实效的根本原因。下面将就此时此地在道德教育上特别强调和特别严重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官方制定的道德生活教育的目标第一条第一句就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小我指个体,大我指全体或国家。个体与全体之间是个极复杂的问题,一百多年来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为了二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争论不休,所持的立场壁垒分明。这个问题在政治思想里,就产生自由与权威的问题;在伦理思想里,就有权威伦理与人文伦理的不同。在儒家的传统里,五伦之教属于人文伦理,西汉董仲舒为适应专制体制而主张的三纲伦理乃权威伦理。假如今天我们仍要坚持权威伦理,则无话可说;假如我们要重整人文伦理的精神,就必须肯定人自身就是目的,道德价值仅能就着人自身的利益而决定。而人自身的利益中最重要的乃是他能力的解放与创发性运用,这样所谓“小我”中就涵盖着“大我”的要求,不是要“小我”臣服于“大我”,成为“完成大我”的工具。“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这种律令式的要求,只有在极为特殊或非常态的状况下,才是必要的,例如战时向将士们的要求。如把非常态的视为常态,或企图以非常态的代替常态,则必使正常的道德教育导入歧途,我们道德教育上一部分的问题正是出在这里。
在《青年训练大纲》里,为了“确立国家高于一切之信念”的目标,其实施要点是:“(向青年)讲述先有义务,始有权利之理论及例证”。不知道我们的教师依据这个实施要点能提出何种理论与哪些例证?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所谓权利包括人所有的基本自由。人的基本自由或权利是“宪法”所保障的,绝非以“先有义务”为其条件。“国民”如不尽服兵役、纳税等义务,自应受法律的制裁,但并不因此而丧失全部的权利(如因服刑而失去行动的自由,但仍保有不受刑罚的权利)。有时候权利和义务是一体的,如“宪法”第二十一条:“人民有受‘国民’教育之权利与义务”,试问:在这里义务与权利如何分先后?“宪法”第二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因此如真有“高于一切之信念”的话,也只有“‘国民’全体”足以当之,而非“国家”,所以“确立‘国家’高于一切之信念”,也与“宪法”的民主精神不合。如果我们真想训练青年成为一个现代公民,教他们理解“宪法”、熟悉“宪法”,不但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而且有其必要,其他生活上与道德上的要求,也不能与“宪法”抵触。
服膺权威伦理者,其施教的方式也必是权威式的。学者们基于时代的不同,一直呼吁各级学校的训导工作应尽量避免使用权威的方式,而代之以合理的辅导,但几千年的老习惯,要改变谈何容易?何况我们还一直把军事化教育与训育工作混淆不清,自然更增其困难。
就理论而言,“权威”并非都是坏的意义。弗洛姆有理性权威与非理性权威的区分,理性权威是靠一个人的才能与成就,并建立在相互信托的平等关系上,他不需要运用任何非理性的威势来恐吓别人;相反地,他会要求对方经常提出质疑与批评。非理性的权威多半是以权力慑服对方,并利用对方因恐惧而感到不安无力,而加以控制。我们这里讨论并希望改变的是后者而非前者,前一种权威不但是人成长(包括心智与人格)所必须,而且对德行的培养很有助益。
非理性的权威运用在教育上——尤其是道德教育,其弊害是相当严重的。因这种方式总是要求对方屈从,一个人一旦屈服于非理性,其本身就已表现出道德的堕落。屈从代表自我意志力的丧失,假如习惯于这种领导方式,他对权威所指定的信念或真理,会失去反省和批判的能力。他只听信权威的话,再也觉察不到内在的良心之声。这种人生活在社会上可能完全失去保护公正,反对不义的基本反应。
人之可贵在他具有理智与良心两大天赋的潜能,教育的最大目的,就是经由合理的途径去激励它、发展它,并能有效地运用它。理性的权威使人心悦诚服,这种方式有利于天赋潜能的创发,而创发性的乐趣远比高压性的惩罚及道德性的训诫更具有伦理上的教育意义。
……
书摘二
摘自第六章《中国人的家庭与家的文化》(李亦园):
财产与企业的继承法则
我们已经说明了日本人倾向于把“家”看做是一个企业共同体,而家族成员不过是这个共同体的附属品而已。中国人则倾向于把家户或企业当做是系谱上的家族成员之附属品。这种差别反映在当前的企业发展方向时,在日本许多由家族所创办的中小企业就比较容易走向公司化的正常途径,我们可称之为“家族企业化”。中国式的私人企业往往不仅家族的控制日益强化,甚至有些原本相当健全的公司也沦落为家族企业的体制,走的是“企业家族化”的方向。这类公司即使股票已公开上市,其经营权仍然大部分为家族关系所垄断。
日本人对于家的共同体之重视,相对地减轻了血缘传承的重要性。所以,一家之主(家督或家长)的代代相传可以不必受血缘系谱关系的限制。因此,日本所谓“亲子”关系并不局限于血缘的父子关系。真正的父子只有辅以实际的继承关系才被认可为名分上的亲子关系。作为儿子的不见得即自然获得承继父亲之“家”的权利,而被认定为具有“亲子”身份关系的养子反可以继承家督之地位。
在日本相当普遍的“婿养子”观念最能够显现出此种非血缘的亲子关系。在中国只有“赘婿”而无“婿养子”,赘婿被招入其岳父家时,并不改姓,也不能继承其财产,死后其神主牌不能入祀其祠堂或公厅。所以,中国有句俗话“传媳不传女”,意思就是说只传给属于自己宗祧的后代,把女婿也排除出去了。而日本的婿养子不仅是女婿,且在一进门之后即为养子,更改为妻家的姓,完全取得继承妻家家督的地位。近代在政界上颇为有名的例子——岸信介与佐藤荣作,原为亲兄弟,荣作因入赘佐藤家而改姓。
工商界的例子更是唾手可得,例如伊势丹百货公司的创始人小菅丹治(1859—1916),原名野渡丹治,后为伊势屋米谷商小菅又右卫门之婿养子。“伊势丹”之名即取自“伊势”屋和野渡“丹”治。第二代小菅丹治,原名高桥仪平,是第一代小菅丹治之婿养子。武田药品公司在1781年的创办人,原名竹田德兵卫,后成为近江屋长兵卫(以店名或家名为姓之例)的婿养子,袭其名近江屋长兵卫而为武田药品初代老板。第二代近江屋长兵卫为初代之二男,原名熊三郎。第三代近江屋长兵卫是初代长兵卫之弟(即第二代长兵卫之叔父)的二男,原名富藏。再看丰田自动车工业的创办人丰田英二家之系谱,历任社长为丰田佐吉→丰田利三郎→丰田喜一郎……→丰田英二。丰田利三郎原姓儿玉,入赘为丰田喜一郎之妹夫,但因比喜一郎年长,故反成为家督承续者。死后方由喜一郎继任为社长。战后经过两任非丰田家成员任社长,1967年再由丰田英二(丰田喜一郎之堂兄)继任。
从系谱看起来,这些历代一家之主或老板的关系与血缘的父子关系实有相当的距离。简言之,“家”的继承法则中带有相当程度的选择性,而不拘泥于真正的血缘关系。此种弹性使得“家”常能选择能力较强的继承者(Cf.Ohibusq 1978:164)。有人把日本的“家”比喻成中空的竹茎,意思是说日本人的家像是一根竹子笔直地伸长,外壳非常坚硬,内容却空空的,没有血缘的内涵。家宅、家名和家业是永久存在的,可是几代以来住其家、袭其名、从其业的人彼此之间可能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Watanabe 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