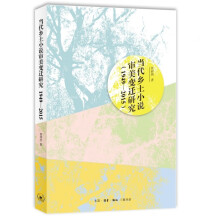与西方唯美主义者不同,“海派唯美主义者”则延续着中国一贯的崇尚自然的审美传统。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因“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生发的敬畏自然之心思与表现自然之美的传统,因而,在中国历来的审美活动中,物我之间的界限不断被消弭,大自然往往成为主体审美体验与审美情感投射的中心对象,山水、花鸟、田园风光等自然景观在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之中不仅仅是被描绘的对象,而且是熔铸着主体情感体验、理想追求和人生境界的生命活物,他们所追求的也不仅仅是简单地描绘出自然之美,还要努力达到与自然生命契合无间的“天人合一”式理想境界。在对这种境界的不断追寻之中,不仅形成了中国文人独特的审美心理机制,也衍生出一系列的诸如月亮、流水、梅兰竹菊等经典的文学审美意象,这在邵洵美的早期唯美诗歌中体现得即尤为明显。邵洵美等“海派唯美主义者”在把“自然界的一切”视为“文艺创作的最好的材料”①的同时,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敬畏与膜拜自然的情感,他们认为,“自然的一切和诗是同样的神秘,你只能去领会,不能去解释;你只能去欣赏,不能去模仿”②。这一看法同样与中国传统的自然审美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的文人作家看来,自然事物变化莫测、形态各异,自然之美更是异彩纷呈、难以穷极。不仅如此,即便是同一自然事物,其色彩、形态等所呈现出的美学效果也会因时、因地而异,郭熙在《山水训》中所谓的“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欲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即是对此很好的诠释,因此,任何的艺术表现形式在真实的自然之美面前总难免存有缺憾。正是基于对自然之美丰富性与神秘性的洞察与把握,“海派唯美主义者”作出了有别于西方唯美主义的价值判断:并非是自然模仿艺术,而是艺术模仿自然,并且艺术模仿只能是无限接近于自然之美而达到所谓的“化境”,不可能达到或超越自然之美,自然美高于艺术美。在文艺创作上,海派唯美文人则摆脱了西方唯美派只重人工的单一创作模式,而是崇尚火一般的生命情感的毫无顾忌地自然宣泄,极力捕捉万事万物的生命本真之美。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