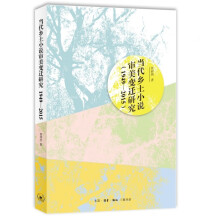对于当代中国美学来说,过去三十年里有两方面大的倾向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审美研究”为中心的各种理论建构;二是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借力“文化研究”而获得迅速展开的审美文化批评。在这两方面倾向中,其实都存在一个“如何确立感性自身意义”的问题。在前者,“感性”问题主要被置于审美认识系统中来把握,即如何和怎样在同人的认识理性的关系方面,发现感性活动在审美中的具体存在,进而选择和确定其在美学上的结构性位置。在这个意义上,“感性”问题对于当时的中国美学来说还是一个认识论话题,80年代中国美学也因此基本属于哲学内部的认识研究范式,包括当时非常流行的各种审美心理研究、审美教育研究等,大体都没有脱离审美认识系统框架。在各式各样强调“审美研究”的美学理论中,“感性”的存在价值具体体现在它与人的认识理性的对应关系上;“感性”的完整性和丰富性,不能离开理性在审美认识系统中的确定性和规范性。就此来看,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以追求建构“完备”的体系化理论为目标,正适应了这种需要——它既合理地强化了美学作为哲学认识论的学理身份,又弥补了过度张扬人的认识理性的美学理论之结构性缺失,向当时的中国美学和美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建构前景,实现了“拨乱反正”时期中国美学对人的审美权利的期待。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于借助“文化研究”而展开的审美文化批评活动来说,“感性”问题却超越了一般认识论层面:“感性”在这里并非一种结构性存在,也不是同认识理性处于直接对应关系中的存在;它被归于人的当下生活语境,是人在现实中的生活情感与生活动机、生活利益与生活满足的自主呈现,同时也是人的直接生活行动本身。在这个层面上,“感性”体现了与整个认识系统的关系疏远化、与人的认识理性的关系间接化,既不再具体受制于认识理性的制度性要求,也不仅仅囿于其自身作为认识本体在审美认识系统中的既有位置,而是以一种自然存在的方式作用并显现为人的直接现实生活形态。因此,对于在文化研究系统中展开自身的审美文化批评活动来说,“感性”问题的存在论特性才是根本——尽管它的认识论性质依然不可忽视,但问题的核心已经发生转移,不再是一般意义上如何确立感性在哲学认识论系统中的结构性身份,而是如何在感性的现实呈现中确立“感性意义”的独立形象。
这样,我们发现,在审美文化批评中,“感性”问题其实具备了两方面看似对立实际在共同文化语境中相互关联的特性。首先,在当下生活实际中,“感性”并不构成认识系统的存在本体,而是作为当下存在现象直接呈现着,所以,在审美文化批评层面,“感性”问题同作为认识系统主导因素的认识理性之间并不发生直接对应关系,具有相对于认识理性的间接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人的认识理性的规定性来责备当下现实中人的各种感性满足和利益实现要求的非正当性,不免有些文不对题。在人的当下生活层面,感性的生活情感与意志、生活利益与满足在形式上是自足的,在内在性方面则是自然合法的。由此,在审美文化批评活动中,“感性”问题根本上体现了一种由感性与理性关系的间接性所造就的非对抗性质。感性存在的自足性并没有直接破坏理性在认识关系上的绝对性,而理性在认识系统中的权力同样也不可能自动生成为当下生活的必然性干预力量。
其次,在审美文化批评范围内,“感性”问题体现了相对于人的当下生活的直接性。“感性”问题生成于当下生活过程,在很人程度上就是人的当下生活本身,当下生活活动的存在形象通过“感性”方式获得具体呈现。就像手机的使用功能离不开手机的品牌形象价值及其不断翻新的外部造型,人的各种当下生活动机、利益也同样呈现于生活本身的实现形态之上;当下生活的存在意义,决定于它所能获得的感性呈现方式、所能实现的感性呈现结果。这样,在人的当下生活动机、利益与其满足实现之间,便基本上不存在认识上的中介环节,可以直接通过生活的感性存在形象得到有意识的确认。显然,这种相对于人的当下生活的直接性特性,一方面具体表达了当下生活本身巨大的感性实践功能,另一方面则生动再现了当下生活与“感性”问题的同质化过程,从而也决定了审美文化批评活动必须超脱一般认识论,放弃对认识理性的固有信仰与理论执着,从当下生活实践本身出发去阐释生活的感性功能,介入人的当下生活之中体会生活满足的实践形象。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