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太注重他个人在当代思想界的地位,才有抱怨之情,他没有看到,其实他当初的路子,不但没有被淡忘和抛弃,反而已经化为学院中的主流、产业,乃至体制。他的主体性哲学,无非是用当代国外各种新思潮新理论补充发展马克思的学说,给马克思主义冠以新名称或加上新的形容词。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中国各个大学,不知道有多少教师在“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之类的名目下从事各种各样的“课题”、“项目”、“创新工程”,乃至建立“基地”。
其实,在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如日中天的80年代,另一种路数完全不同,预示了今天思想界方向的思路已经萌芽出土。1981年,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发表题为“试论霍布斯的政治学说”的论文,1986年,北京大学另一位研究生发表题为“评卢梭人民主权论的专制主义倾向”,他们的观点远没有李泽厚的观点有影响,首先是因为他们尚未出茅庐,没有什么话语权,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比起李泽厚的思路,他们的思想太过超前,脱离中国人的接受水平。直到90年代,王元化发现了顾准思想的价值,将其概括为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才有直到今天还方兴未艾的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思想史的根本性反思。这是更有价值和生命力的思路,真正切中中国问题要害的思路。李泽厚80年代的思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在今天为万千人提供了俸禄,带来万千甚至更多的课题经费,以及学术研究中泡沫式的热闹,但思考中国命运的思路是另一条。
李泽厚的学术思想感觉实在是好,他在《告别革命》中说,他在1978年就提到了法国式和英国式革命之分。看来他对这里说的另一种思路并不隔膜,但无论如何,他的着力点和影响完全不在这里。他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大学文科教育中最为出类拔萃之才,他没有顾准、王元化那种现实的“疼痛感”。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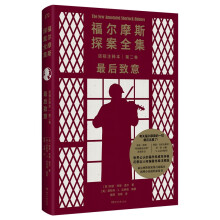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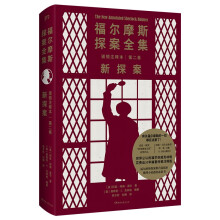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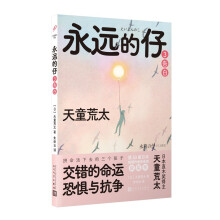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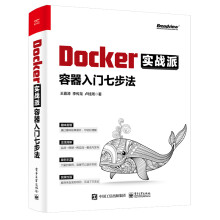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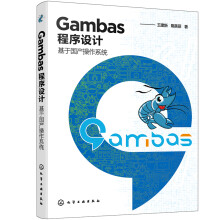
——臧棣《诗歌·海子:一个巨大的诗歌文化熔炉》
像我这样的人,讨论公共话题,抨击这个,批评那个,总得顶盔带甲才行,照照镜子,感觉像个武士了,才踏实,虽然知道自己其实就是个堂·吉坷德,无非是拿着扎枪跟风车作战。可韩寒不是这样,他只是顺便捡起一块石头,顺势对风车扔过去,其实并不在意将风车怎样了,只是石头扔过去,碰巧碎片溅进轴承,还真叫这风车难受上好一阵子。
——张鸣《思想者·韩寒:抵抗体制的新生代寨主》
思想总是以一种吊诡的方式进入社会生活,孔孟如果看到明清皇帝一边尊孔一边大兴文字狱,不知要如何痛心疾首。马恩如果看到斯大林一边尊马列一边搞屠杀,不知要如何目瞪口呆。因而,这个时代
需要的,不但是浓重的历史感,而且是哲人的审慎。
——陈壁生《国学热:传统文化何以复兴?》
我也经常改同学何的论文,这一代啊,在网络知识唾手可得的时代,他们再不用推敲文字,通篇都是拾人牙慧。我觉得好可惜,这样下来,他们如何能够理解王小波在《我的师承》里谈到的汉语的韵律和诗意,又如何赢得“远离偏执,从建设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中获取幸福”这种思维的乐趣?
——艾晓明《小说·王小波:一代人的精神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