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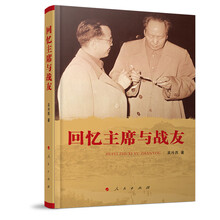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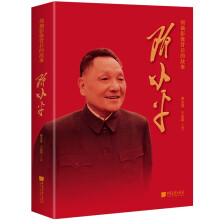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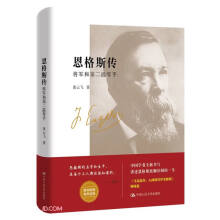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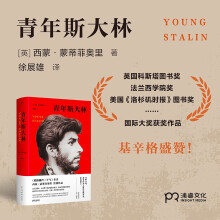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
他,身无分文,外出游学,仅靠卖字、写信做社会调查式周游,“欲以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他,勇闯“虎穴”,为民请命;
他,作为学生会总干事,率领学生志愿军,智夺北洋军枪械;
他,寻求“改造中国和世界”之路,成立新民学会;
他,斗“汤屠”(北洋军阀汤芗铭),驱“张毒”(北洋军阀张敬尧);
他,亲率泥木工人大罢工;
他,……
于同窗中,见知己;于困惑中,见探求;于风雨中,见搏击;于寻常中,见非凡。
——他,就是毛泽东!
——这,就是他的青春岁月,燃烧的青春岁月!
毋庸置疑,毛泽东是个奇人。非常之时,必有非常之人。20世纪初,是新旧社会体制此消彼长,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以枪炮征服中华帝国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险恶时代里出现的一个奇人。著者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上,以文学的笔法叙述和描写毛泽东其人其事之奇:他的远大志向、奇谋远略、缜密思维、深沉感情以及指挥若定的领袖气质。一桩桩奇事,烘托出一位锐志革命的奇人,以及他的许多志同道合的师友。
《青年毛泽东》分为二十四章,详实而生动地记述了青年时期(1910年秋—1921年夏)的毛泽东,身无分文,外出游学,“欲以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勇闯“虎穴”,为民请命;置身雷雨中,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率领学生志愿军,智夺北洋军枪械;寻求“改造中国和世界”之路,成立新民学会;斗“汤屠”(北洋军阀汤芗铭),驱“张毒”(北洋军阀张敬尧);结识陈独秀、李大钊;……从一个寻常的进取学生,在一步步有心的磨砺中,在大社会与大自然种种“有情”甚而残酷风雨的洗礼下,历经迷途中的困惑、尝试中的失落、破碎中的痛苦,在万般悲欢离合的锻造下,逐步成长为一个“新民”,一个寻常又不寻常的忧心报效国家与民众的学子——志士。客观、真实、全面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毛泽东形象。
1911年的中国是多事之年。你看湖南这条母亲河——湘江,就躁动着,汩汩然,不安地滚滚北去。
一声汽笛,划破凄迷的雾空。
但见一艘小火轮,颠簸在浩浩波涛之间。
仿佛是应和着汽笛的召唤,从嘈杂的小火轮三等统舱里,走出一个拖着长辫子的青年。蓝灰的粗布短衫已泛白,长裤是白粗布,蹬着黑布鞋。人瘦高,脸开阔,那敞达的前额下是一双探求的眼睛,明澈而执著;端正的五官透出山乡人特有的敦厚和聪睿。时年未足18。他便是毛泽东,字润之,后来成为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他掮着包袱,踱到舷口,新奇而贪婪地饱览着这条早知名而从未见过的湘江——
凄迷的惨淡中,白浪滔滔。
毛泽东又抬眼远眺着从未曾到过的长沙——
看那岸头,屋片片,人点点,跟自己韶山的家乡就是不一样。
随着老少乘客欢欣的叫唤,船舱里掀起一阵阵忙乱:
“快看、快看,长沙城!”
“到了!总算到了!”
毛泽东的自述:“我第一次远离自己的家乡,去到一百二十里外的长沙——那可是湖南省的省会!听说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总之,是个很繁华的地方。我向往,又兴奋。可我又不晓得等待我的会是个什么命运?……”
汽笛催鸣。
小火轮正驶近码头,猛听得江中突起惊叫,准备下船的乘客莫不心下抽紧,急急循声探顾——
只见一艘悬挂着太阳旗的快艇,长驱直入,将躲避不及的两只小划船先后撞翻了。
“蠢货!”随即留下一串浪笑。
“救命!——”
毛泽东几乎未及思索,包袱一放,纵身入水,用山里人独特的侧泳,向跌落江中的一对老小游去。几位船工见状,也相继跳入水中救援。
“快停船!停船!”
驾小火轮的舵工兴许是看到了险情,即可将小火轮慢慢停下。
毛泽东和船工在水里扶托着救起的一对老小,在乘客的拽拉下,推送上船。
船上又是一阵忙乱:
“快快,到舱里去暖暖。”
“这小日本,霸占了我们台湾还不死心!”
“哼,还连带着钓鱼岛和黄尾屿、赤尾屿呐!”
“欺人太甚!”
“真可恶!”
但见码头上,招摇的“太阳旗”颇为刺目。日本快艇已经抵岸,一对荷枪日军吆喝着,亟亟冲上岸去。
还在水里的毛泽东不能不抽起心,谛听着船上纷纷的议论:
“狗日的,我大清王朝是怎么了?!……”
“嘘!不要命了?城里正抓剪辫子的革命党呐!”
毛泽东不由自主地斜首捏过长辫子,沉吟着,又一睇岸头,不觉蹙起双眉。未几,他撑身爬上船,顾不得浑身精湿,掮着包袱,依然禁不住放眼饱览一番久所神驰的省会……
“果真了不得,比我们韶山大多大多了;哎哟,好气派呀!”
骤然间,心里兴叹着,双眉顿自一拧——
江中,太阳旗的后边,竟是“米”字旗——偌大的英国货轮上,几个洋监工,捏着木棍,呵斥、驱赶着扛送标有“猪肉”、“猪鬃”字样的小箱、大筐上船的中国苦力。
一个个扭曲的腰,一条条耷拉的辫。
毛泽东也不禁下意识地紧捏着自己的长辫子,脑际骤然又闪划出乘客的“天问”:
“我大清王朝是怎么了?!……”
毛泽东眼里波光一记颤动!他再不忍目睹,怫然抽身离去。转到街角头,毛泽东询问了一位测字的老人,恭敬地一鞠躬,便顺着老人指点的手势,踽踽寻去。
老人定睛注视着眼下这位知礼的后生子,想唤住他提醒什么,可又止住了。
眼门前的街面,店铺鳞次栉比:“兴隆绸庄”、“欧亚洋行”、“日清百货铺”、“夜来香茶楼”……
毛泽东顾盼着,好生新奇!
“这许多店铺,那得要多少人来买呀!”
正寻思着,忽听得什么隐隐的骚动,毛泽东还不知所以,却已见得一些个店铺,如临洪水猛兽一般,仓皇地上起排门。
“快快!”
“又闹事了?!”
“怕真要亡国灭种啦!”
毛泽东下意识地一怔,心里念叨着:“怪事。又怎么了?!”
在十字街口,一大批饥民与赶来的日本兵撕扯着、扭打着,另有一批饥民依然不管死活地从日商米铺里抢背着一袋袋、一桶桶米出来。
穿着和服的矮胖老板气急败坏地叫骂着。同时间,日军开枪了。有人即刻倒在血泊中。
“清军来了!”
不知谁一声报讯,饥民们闻风卷出,却没有逃得了,还是被日军、清军双双截住。
一个清军管带,赶到日军跟前致着歉,日军指挥官并不领情,信手一记耳光:
“八格牙鲁!”
“喳!”管带认着罪,转而喝令下属:“还不给我动手?”
一队清兵闻命出手,横枪挺刀,围捕开饥民。
正是三方舍命厮杀之际,不知从何处又卷来一股已抢得大米的饥民,只见没有辫子的首领响呼一声:
“快走!”
“抓住那剪辫子的!”
一股清军扭身抓捕。
逃的、追的、喊的、打的,一场混战。
毛泽东见所未见!蓦然,他眼光一跳——
一个扎着小辫子的细妹子,饿得全不顾眼皮下的凶险,捧着洒落在麻石子路上的生米猛嚼,不承想清兵的洋枪已冲她后背刺到。
毛泽东急中生智,抓起一把米,冲清兵脸上撒去,趁对方抹眼分神的转瞬之机,一个箭步,抱起细妹子就跑。
奔到拐角口,毛泽东见到收摊的小贩,这才停住步喘息着说:“来个冻米团。”他递上五个铜角子,接过冻米团,塞给细妹子。
细妹子几不敢信地直瞪着眼,犯着傻。
“没有事,快吃。”毛泽东警惕地扫一眼邻街的厮打,牵过细妹子迅即离去。“你叫什么?”
“朱华贞。”
“朱华贞?硬是个好名字嘞!几岁了?”
“八岁。”
“你妈嘞?”
小华贞立即泛出泪光,嗫嚅着:“饿死了。”
毛泽东心下顿自一抽。少许,又叮问:“你爹嘞?”
“爹养不活我,要……要送我给姨妈……”憋迫的泪珠终于从小华贞的眼眶里溢泻了下来。
毛泽东抽起的心亦不禁颤动了!
“贞妹子!”
一响从天而降的招呼,不啻细妹子,就连毛泽东也心下一跳。双双回首——
追来一位三十开外的男人,人瘦削得近乎干瘪,又脏又破的长袍子,残留着几分落魄秀才的模样。他叫朱辛贵。
“不。爹,我不去姨妈家!不去——”小华贞恐惧地啼叫着,直往毛泽东身后钻。
“不去了,不去了。爹又有事做了——明天就去教书;我们……有饭吃啦!”朱辛贵愧悔之下,有点言不成语。
“噢,这就好。”毛泽东这才宽下心来。“再穷,也莫把自己的亲身骨肉送出去哇。”
“是,是的。这鬼世道,把人都逼疯了!”朱辛贵连连颔首,发现女儿捧着冻米团,感愧的目光不觉又投落到陌生的好人身上,“先生是?”
“我不是先生,是来投考湘乡驻省中学的。”
“噢,离寒舍不远。”
“我认得!”小华贞正愁没法答谢,一下昂起小脑袋。
此刻抢米的饥民还在四下溃逃。汹汹的日军、清军仍在满街追捕。
“走这里。”机灵的小华贞拖过“大朋友”的长手,钻入灯柱边头的小巷子。
小华贞与父亲一直将毛泽东送到新安巷的湘乡驻省中学大门口。
“有劳二位了。”毛泽东从包袱里取出一小串铜钱。
朱辛贵眼珠子下意识地盯着,手上仍不失理智地推辞着:“不不,这万万……”
“你还没有去教书,父女俩还得吃饭呀。”毛泽东不由分说,将钱往对方手里一塞,又一捏,便返身入校。
是一位不惑之年的校长在自己办公室里接待了毛泽东。校长鼻子尖,脑袋大。他细细看罢引荐信,定定地打量着眼下这位显然高过常人的学生说:“东山小学堂,倒是很赞赏你哇。”
口气里,流露出明显的怀疑。
毛泽东听出话中余音,唯恐被拒之门外,赶忙“申诉”:“校长,我可是百里求学,就不能让学生试试?”
“唔。那就先来应考,试试看。”
湘乡驻省中学算得是省会的名校了,慕名而来的考生济济两屋子。
考场上,有的把笔凝思,有的虚汗不止,有的搔首挠耳,似乎人人都很有些紧张。
毛泽东已忘情个中,挥笔如流……
毛泽东的心潮奔涌着:“呜呼,朝鲜沦陷,台湾沉亡,越南丧失,缅甸覆殁……”
许是东山小学堂的引荐,许是下意识使然,大脑袋校长于次日有心调出了毛泽东的试卷,亲自审阅。
四邻岌岌。中国亦会步其后尘而灭亡吗?中国有句古话——“前车
之覆,后车之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