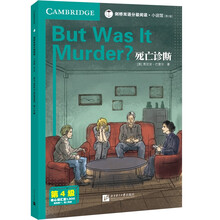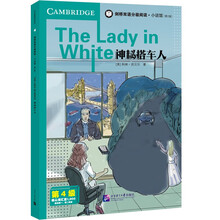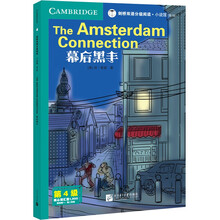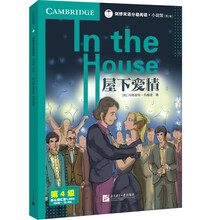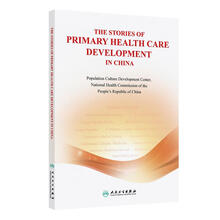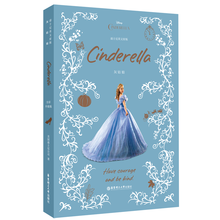那是我们第一次到英格兰,天很冷,即将来临的便是冬至:白昼最短的一天。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可能是4岁,或者是四五岁的样子。那次航行我似乎仍然记忆犹新:那混浊发绿的海浪,随波荡漾的泡沫,12月的海与天暗淡的交融,一闪而过的海鸟和往来航行的船只,这一切依然历历在目——虽然只是一些破碎的记忆,却是那么难以忘却。<br>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曾经住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事促成了这次旅行?混沌的记忆不能帮她解答这些问题。她在人行道上努力地思索着,一会儿把手放在嘴唇上,一会儿眨眨眼睛。最后她打开她的编年史,在发黄的纸页中翻看那苍白、简洁、支离破碎的记录:她能读到的好像只有这些——我来自这样一个地方,那里高楼林立,雄伟壮观,白色的房屋前到处都是挺拔如塔的树木。还有条宽阔平坦的、走不到尽头的大道。那个时候在这条道路上,卷起过两股潮流:一股是步行者的潮流,他们穿着绣有粉红色玫瑰花的衣着,披巾随风飘动着,小阳伞像郁金香一样赏心悦目;另一股是马车的潮流,轻快而又安静地向前涌动。在那条马路上一切都在进行着,却是在安静中进行的。那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到处都是人,但并不吵闹。<br> 我们住的房间里地板光滑,没有铺地毯,里面有许多镜子和窗户。在这幢房子里,我非常确切地知道有一个房间,门上嵌着紫红色的玻璃,它那斑斓的反光照映在门对面的阴影中。这扇明亮的大门通向一个小巧的绿色花园,那里有草坪,朵朵鲜花和一棵大树。花园里一片葱绿,到处都挂满绿色的叶片,而这片片绿色主要还是那些——我知道那是葡萄藤,因为我还记得那一串串葡萄和弯弯曲曲的藤蔓……<br> 我们跟谁一起生活?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只能是跟我的父亲。对于他的事,我能记起一二十件,但都是模糊的、支离破碎的。我的父亲——我当时叫他爸爸——是我童年时代所受的一切惩罚的诱因。我总是不明事理地希望和他能多待一会儿。为了做到这一点,每当负责照看我的保姆转过身去时,我就会悄悄地溜出育儿室去他的书房。然后我就会被逮住,身子被摇晃着,有时还挨揍,然而那都是我应得的。我的父亲是否了解我多么珍惜与他在一起的机会,这我不敢断言。他整天忙忙碌碌,经常出门,即使在家里时也总有别的乡绅与他待在一起。不过,黄昏时他总是会突然进入育儿室,走到我的小椅子边,站上一会儿,低头朝我看着。当我兴高采烈地伸出手臂时,他会俯身把我抱在胸前,说道:“波莉,现在可以下楼做爸爸的小客人了。”<br> 爸爸有一种灵活而有趣的谈话方式,很容易使我幼稚的头脑有所明了,让我天真的心灵感到兴奋。当他教育我时,显得非常有魅力。我觉得他的性情有点急,甚至有些暴躁,但他对我确实很温柔,对别人却不总是这样。我记得他既性急又严厉,但对我从来不是这样。我从不惹他发怒,也从来不担心他会生我的气。我多么想用我的小手摸摸他黝黑的脸颊,站在他的腿上,梳梳他的头发,或者把头靠在他的臂弯里呼呼地睡上一觉啊!<br> 刷墙<br> 〔美〕马克·吐温<br> 星期六的早晨到了,夏天里,整个世界都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生机勃勃。每个人的心中都荡漾着一首属于自己的歌,年轻的人儿们会情不自禁地哼起属于他们的旋律。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欢笑,每个人的脚步都是那样地轻快。洋槐树上的花儿正在盛开,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芳香。<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