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回到我们本章开头的问题:
“人的性格究竟可不可以改变?”
恐怕大多数中国人对此都持否定态度。其实,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心理误区了。
以我自己为例:
我父亲原本是个农民,20世纪50年代参军入伍,提干以后,他的大半辈子都献给了部队和我国的国防事业。我母亲也是农民,同样是50年代棉纺厂招工应聘来到城市,一个纺织女工通过自己努力入党提干,成为管理几百人的车间支部书记。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人都非常朴实、内向,不善言谈,也不善交际。
记得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他们都是诚惶诚恐。
“坐,喝水吧”,然后就没话了。
要不就是“来,抽支烟吧”,又没话了。
搞得客人很尴尬,他们也手足无措、相对无语。
很多老战友、老部下、同乡、同事,我也很少见他们主动联络,常常是人家“上赶着”来探望他们。由于经常出现上述场景,久而久之,人家也就不来了,因此浪费了很多社会与人脉资源。我曾批评他们与外界“老死不相往来”,其实别人来他们也蛮高兴的。归根到底,我得出结论:性格使然。
而我的性格则和他们截然不同。
记得那是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去父亲单位找他,和他同一个办公室的叔叔说:“不会吧,老张,这是你儿子吗?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怎么一点儿也不像你。”
我心里话:“我爸为什么不能有我这样的儿子,你生气吧你!”
但平心而论,那位叔叔说得不是没有道理。
论长相,我长得像我妈,自然比我父亲好看;论谈吐,毕竟刚大学毕业,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彬彬有礼而又出口不凡,不像我爸——“三棒子打不出个屁来”(我妈语)。
我的朋友很多,没有一个人不说我“外向”的,就连我的同事、同行甚至部下、学生,也都评价我是个“性情中人”。
性情者,自然是“喜怒哀乐均形于色”。
而形成这种性格的根本原因,我认为后天环境的作用要远远大于遗传的作用。
因为父亲在部队,母亲工作忙,我出生10个月就被送回河北灵寿老家,寄养在爷爷奶奶家,一直到6周岁全家才一起随军去南昌。这期间,除几次随母亲去南方父亲部队探亲外,我基本上是在村里和小伙伴们一起疯玩儿,爬树、上房、下河沟、看杀猪、起哄,甚至“调戏”小女孩,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调皮捣蛋,坏事做绝。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幼年的早期经验对我性格的形成不能不说是“因祸得福”。假如我始终在父母身边的话,绝对不会像在乡下那么自由自在,任由我的性格顺其自然地自由成长和发展。而到了南昌以后,又开始了我的学生干部之旅,从小学当班长,到大学担任班长、大班长、学生会主席,担任学生干部,自然很锻炼人,因而对我性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再来谈一下理论。
“性格”一词,本身就是个很“虚”、很笼统的概念,无论如何定义,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考量,我们接触、观察一个人性格如何,主要还是看他(她)外在表现出来的态度、言语、举止和行为。也就是说,通过这些外在表现出来的态度、言语、举止和行为,我们才能得出一个判断和结论,也即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所分类的“内向”或是“外向”。而一个人的态度、言语、举止、行为又受什么支配呢?毋庸置疑,是受一个人的“认知”也就是观念和理念所支配的,因为从心理学意义讲:认知决定态度,而态度又决定一个人的言语和行为。
再回到前面所举的例子:
大学生们看到自己的辅导员穿了一条漂亮的裙子:
A:哇,老师,你好漂亮哦!
B:(无语,也可能笑笑。)
C:(无语,不屑的目光。)
A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其背后的认知为:“每个人都需要赞美。”
而B的认知则是:“我夸老师别人该说我拍马屁了,还是不说为好。”
C的认知:“一把年纪了,还这么臭美,那个马屁精更讨厌!”
由此可见,面对同一件事或情境,不同的认知会导致不同的态度与行为。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基本判断:
A:性格开朗,外向。
B:性格沉稳,内向。
C:性格孤僻,忌妒心强。
于是,我们也可以这样推论,假如B和c同样也持A的认知:“每个人都需要赞美”或“你尽可能去赞美别人,而不要在乎他人怎么说”,那么,B和C的性格不也和A一样变得健康和阳光了吗?!
亦即:认知改变一态度改变一言语和行为模式改变
而一旦一个人言语和行为“模式”发生改变,其“性格”不也随之改变了吗?
所以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过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心理误区而已。尤其是对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形成阶段的青少年来说,其性格的“可塑性”极强,有时甚至可以出现180度的大转变,这在现实生活中也极为常见。也正因为这一时期,孩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的看法正在形成,父母和老师的正确引导就显得格外重要和关键。
很多研究资料表明,中国人整体的“民族性格”正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被动”变为“主动”,由“他主”走向“自主”,由“忍耐”变为“展示”。
其实,与父辈、母辈们相比,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又何尝不是在突飞猛进地改变与进步着?这一点,想必大家都感同身受。
可见,性格完全可以改变,只要我们愿意改变!P8-11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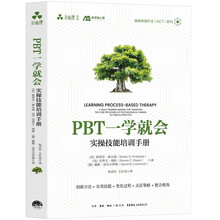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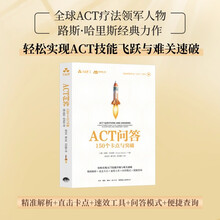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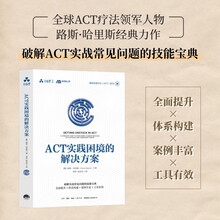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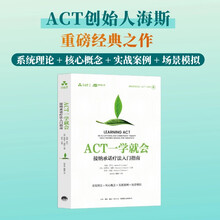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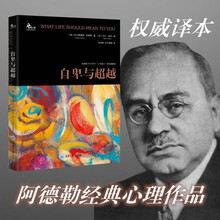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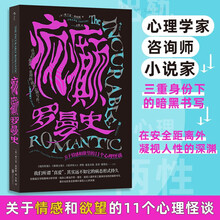
——张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