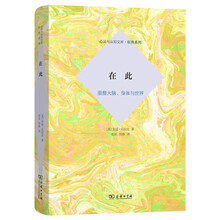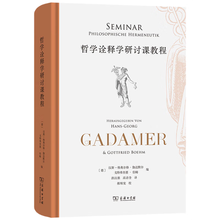当然,哲学家的责任心驱使我们警戒所有理性的谬误。但是,就像礼拜一早晨来的传教士答应承担他前一天诅咒的那些罪恶一样,我们自己却罕能从精神偶像中拯救出来。有时这种谬误被有礼貌的合谋给忽略了——就像当我们允许某部书的作者把所写的最后几页称为“前言”;或者当我们将那些似乎必然预见到了那些迷住苏格拉底之类的赤脚哲学家们的问题的人称作“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一样。在这些情况下,“谬误”似乎既无辜也是无害的。
而且,由于避免诸如此类的理性谬误极端困难,我们甚或会找到忽略它的理由。因为,正像威廉·詹姆士所说:“我们向前生活,却向后思考。”而博尔赫斯则为这一智慧做了补充,他说:“所有的生命都是为时代误置的,甚至人类也生错了时候。”
尽管如此,诸哲学谬误中一个更有害的例子则关涉某种时代错置,即历史被狭隘地理解为追溯某一既定理论结构。历史表述的起因实际不过是该表述的一个产物。这样的目的论史学偏见有: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基督教,当然还有科学主义。这不仅是理性谬误一种更具毁灭性的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最难避免的形式。因为,如果我们想在某一历史描述中获得一致性,就必须求助于意义的某种模式,自然需要将该模式上升为系统知识的相应目标。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