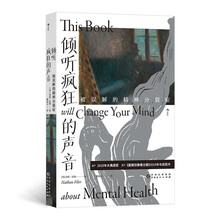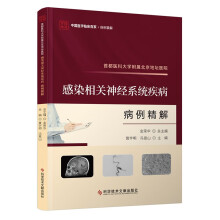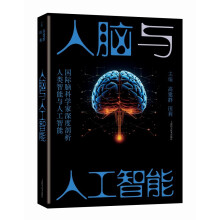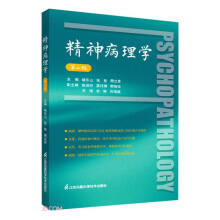有一天,我与人聊天,谈及我们干休所一位老红军干部的遗孀,因精神病出走几年未归,单位不闻不问。我说,这是不负责任,不人道。可对方不同意我的说法,认为她患病出走,无法预防。 “应该将她送医院治疗。”我说。 “她对四邻干扰很大,常常谩骂邻居。”他数落病人的“罪状”。 “四邻应该宽容她,出于人道主义,不要火上加油刺激她。”我以同情的心态说道。 “你们是同病相怜,你去尽人道主义吧!”他说完,扬长而去。 他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虽然我出院已10年了,但我在他的眼里仍定位为“疯子”。从此,我很少与人交谈、争辩。就是与家人争辩问题时,本该我有理,也会惹得对方一句讽刺挖苦的话:“神经病!” “你才是神经病!”我说。 “你说我是精神病,我没进精神病院;你不是精神病倒进了精神病院。” 我无言以对,只好认输。我渐渐地接受了诗人食指说的话:“我把自己定位为疯子。”这样一来,我的心情平静多了,不再为人们说什么“精神病”而激动,不再为别人对自己的态度而苦恼。 乘单位班车,无人与我并肩坐。有一次乘车,刘司机与我并肩坐着,这时有个老兵将刘拉走,并在我眼前,他与刘耳语,示意我是个“疯子”。 我们把有异于正常身体状况的称为病变,也把不同于正常精神状况的称为疯狂,它们可以体现为单纯的数量关系:多数为正常,个别为异常、有病、发疯。疯子的历史地位有过一个从极高到极低的堕落。发现真理之道,一种是理性,其极致是推理和演绎的科学;另一种是非理性,神谕、灵感、顿悟、直觉,都能使我们突然间切入事物的核心。任何一种文明的早期,先知和诗人堂而皇之走在大街上,他们被人们公认能够接受天启和神示,受到尊重。慢慢地,人类开始致力于通过理性工具发现真理,一切不可理喻者,皆被视为异数、怪人、疯子,非理性发现真理之道逐渐关闭。先知基本去了疯人院,诗人还有在外面的,因为他们改为理性思考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