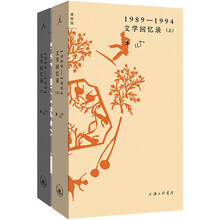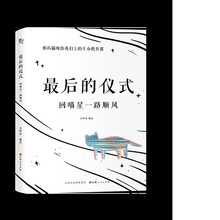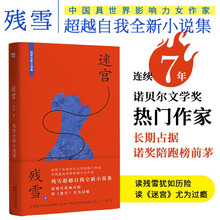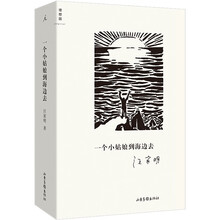张爱玲《天才梦》和《西风》征文奖
张爱玲与文学奖的关系极富戏剧性。她登上文坛之初,就获得了上海《西风》杂志征文名誉奖第三名。相隔半个多世纪,到她逝世前九个月,又意外地获得台湾《中国时报》第十七届文学奖特别成就奖。这一始一终,在其他作家身上是很少见的,可说是良好的开端和比较圆满的结束。有趣的是,张爱玲本人对第一次获奖却极为不满,这就得从她的获奖作品《天才梦》说起了。
海内外“张学”界早已知道,散文《天才梦》是张爱玲自己承认的“处女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曾获上海《西风》征文奖,七十年代收入张爱玲自编文集《张看》。但是,对于《天才梦》获奖详情,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值得探究。
首先当然是张爱玲自己的说法,她在《张看》所录《天才梦》末尾加了一段“附记”,一直不为人注意,现照录如下:
《我的天才梦》获《西风》杂志征文第十三名名誉奖。征文限定字数,所以这篇文字极力压缩,刚在这数目内,但是第一名长好几倍。并不是我几十年后还在斤斤较量,不过因为影响这篇东西的内容与可信性,不得不提一声。
这是张爱玲在事隔三十六年后,首次对《西风》评奖作出公开反应,其弦外之音是颇为清楚的。
到了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在张爱玲的文学生涯即将结束之际,出乎她的意外,深居简出的张爱玲第二次获得文学奖。这次是台北《中国时报》第十七届文学奖特别成就奖,以散文集《对照记》获奖。张爱玲为此写了得奖感言《忆〈西风〉》,这是张爱玲的“绝笔”,文中旧事重提,更明确地表示对当年《西风》征文评奖结果的强烈不满。
据张爱玲回忆,她当时在香港大学求学,“写了篇短文《我的天才梦》,寄到已经是孤岛的上海”应征,“没稿费,用普通信笺,只好点数字数,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不久,《西风》杂志社通知她“得了首奖,就像买彩票中了头奖一样”。谁知等到收到正式公布的“全部得奖名单,首奖题作《我的妻》,作者姓名我不记得了。我排在末尾,仿佛名义是‘特别奖’,也就等于西方所谓‘有荣誉地提及’(honorablemention)”。“《我的妻》在下一期的《西风》发表,写夫妻俩认识的经过与婚后贫病的挫折,背景在上海,长达三千余字。《西风》始终没提为什么不计字数,破格录取。我当时的印象是有人有个朋友用得着这笔奖金,既然应征就不好意思不帮他这个忙,虽然早过了截稿期限,都已经通知我得奖了。”张爱玲还指出:“《西风》后来没有片纸只字向我解释。我不过是个大学一年生。征文结集出版就用我的题目《天才梦》。”这事对张爱玲自尊心的打击是如此之大,尽管她在此文末尾承认:“五十多年后,有关人物大概只有我还在,由得我一个自说自话,片面之词即使可信,也嫌小器,这些年了还记恨?”但她还是强调这件事“成了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隔了半个世纪还剥夺她第二次得奖“应有的喜悦”。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一直到晚年,张爱玲仍对此事耿耿于怀,十分“怨愤”。
第二种是“张学”专家水晶的说法。张爱玲逝世以后,水晶发表《张爱玲创作生涯》一文,文中说到在香港大学求学的张爱玲“偶然看见上海《西风》杂志征文,题目是《我的××》,字数限定在五百字以内,她寄出《我的天才梦》应征,结果被评选为首奖,中途又告取消,变成了第十三名荣誉奖”。水晶还指出:“得首奖的就是后来以写《未央歌》、《人子》成名的吴讷孙(鹿桥)先生。”显而易见,除了吴讷孙(鹿桥)获得“首奖”这一条之外,水晶的说法基本沿用了张爱玲的回忆。
第三种是“红学家”赵冈的说法。赵冈在《张爱玲〈西风〉鹿桥》一文中表示,关于《天才梦》获奖,他的记忆与水晶所说不同。赵冈认为张爱玲征文“原题是《天才梦——我的童年》,而非《我的天才梦》之题。而且所获之奖是‘特别奖’,而非‘荣誉奖’,不是排名第十三名。”赵冈还指出,征文首奖并非为吴讷孙(鹿桥)所得,而是“由一位张姓作家所得,题目是《断了琴弦——我的亡妻》,是一篇悼亡之作,情词凄切,绝非想像出来的作品。吴讷孙先生此时大约还在西南联大读书,年龄不符,似乎无此经历。”赵冈进一步回忆了是次征文前四名得奖作品的题目和内容梗概,强调均与吴讷孙无关,因此有必要“与水晶先生对证一番”。
年代相隔久远之事,回忆总不那么可靠,总会与史实有所出入。张、水、赵三家之说哪家更接近历史真实呢?抑或每家都有部分错讹?经查《西风》原刊,真相方才大白。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出版的《西风》第三十七期刊出《〈西风〉月刊三周年纪念现金百元悬赏征文启事》,从而揭开了这次重要征文的序幕。《征文启事》对这次征文的宗旨、题目、字数、期限、应征资格、手续、奖金、揭晓方式等项都有具体的规定和说明,对澄清三家之说不可或缺,故照录如下:
《西风》创刊迄今,已经三周年了,辱承各位读者爱护,殊深感激。在一年多以前,我们为提倡读者写杂志文起见,曾经发起征文,把当选的文章,按期在《西风》及《西风副刊》发表,颇受读者欢迎。现在趁《西风》三周年纪念之际,为贯彻我们提倡写杂志文的主张起见,特再发起现金百元悬赏征文,并定简约如下:
(一)题目:“我的……”
举凡关于个人值得一记的事,都可发表出来。题目由应征者自定。如:我的生活,我的奋斗,我的痛苦,我的悲哀,我的恋爱,我的婚姻,我的好癖,我的成功,我的失败,我的梦,我的志愿,我的人生观,我的理想,我的世界,我的教育,我的职业,我的学校,我的家庭,我的父母,我的子女,我的兄弟,我的姊妹,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丈母,我的媳妇,我的女婿,我的爱人,我的仇敌,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的老师,我的高徒,我的上司,我的下属,我的衣食住行,甚至我的头发,我的帽子,我的鞋子,我的……,只要值得记述,都可选作征文题目。内容要实在,题材要充实动人。
(二)字数:五千字以内。
(三)期限:自民国廿八年九月一日起至民国廿九年一月十五日止,外埠以邮戳为准。
(四)资格:凡《西风》读者均有应征资格。
(五)手续:来稿须用有格稿纸缮写清楚,于稿端注明作者姓名住址,附寄每期附印于征文启事中之三周年纪念征文印花一枚,并于信封上注明“纪念征文”字样。无印花者虽佳不录。每人所投篇数并无限制,唯每篇须附印花一枚。
来稿请寄上海霞飞路五四二弄霞飞市场四号西风社编辑部。
稿件不论录取与否,概不退还。
(六)奖金:第一名现金五十元,第二名现金三十元,第三名现金二十元。第四名至第十名除稿费外,并赠《西风》或《西风副刊》全年一份。其余录取文字概赠稿费。
(七)揭晓:征文结果当在廿九年四月号第四十四期《西风》月刊中发表。至于得奖文字,当分别刊登于《西风》月刊、《西风副刊》中,或由本社另行刊印文集。
应该承认,《启事》所示征文规则是比较公平和公正的。从《启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爱玲回忆中关键的一点,即征文限定的字数并不是五百字,而是“五千字以内”,相差竟十倍之多!这则《启事》自第三十七期开始,在《西风》接连刊登了五期,照例张爱玲关注《西风》,既要应征,总不至于弄错征文字数,而她偏偏粗枝大叶,写了仅五百字左右的《天才梦》应征。否则,我们今天或许会读到一篇洋洋洒洒,更为精彩的《天才梦》了。
一九四○年四月,《西风》创刊三周年纪念征文揭晓。据该月一日出版的《西风》第四十四期编者的《〈西风〉三周年纪念征文揭晓前言》透露,共有六百八十五篇作品应征,可谓佳作纷陈。“执笔者有家庭主妇、男女学生、父亲、妻子、舞女、军人、妾、机关商店职员、官吏、学徒、银行职员、大学教授、教员、失业者、新闻记者、病人、教会及慈善机构工作人员、流浪者、囚犯等,寄稿的地方本外埠,国内外各地皆有,社会上各阶层、各职业界、各方面、各式各样的人差不多都有文章寄给我们,可见会写文章或想写文章的并不只限于文人学者,同时也可以显示《西风》已经渐渐侵入了社会的各阶层”。然而,也因此增加了评选的难度。
编者宣称“是以内容、思想、选材、文字、笔调、表现力量、感想、条理、结构等条例为准则,以定去取的。”他们“自信确曾用着冷静的头脑,公正的态度,客观的眼光,把投稿者每篇心血之作详细阅读过”,但在“选定得奖的文章,以及决定名次时,还是觉得左右为难”。编者坦陈他们有可能“委屈了一些佳稿”,最后决定在十个中选名额之外,“另外定出三个名誉奖,以增加读者的兴趣,同时减少”他们的“歉憾”。全部得奖名单也照录如下:
第一名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水沫
第二名误点的火车(我的嫂嫂)梅子
第三名会享福的人(我的嫂嫂)若汗
第四名谁杀害了姐姐?(我的姐姐)绿波
第五名残恶的交响曲(我的妹妹)家怀
第六名淘气的小妮子(我的同窗)鲁美音
第七名无边的黑暗(我的回忆)方菲
第八名结婚第一年(我的妻子)吴讷孙
第九名我做舞女(我的职业生活)凌茵
第十名孤寂的小灵魂(我的妹妹)连德
名誉奖
第一名困苦中的奋斗(我的苦学生活)维特
第二名我的第一篇小说(我的小说)南郭南山
第三名天才梦(我的天才梦)张爱玲
拿这个正式公布的得奖名单与张、水、赵三家的回忆相比较,不难发现三家的说法都有错讹。有必要指出的是,三名“名誉奖”的奖金额与第四至第十名的相同,即“除稿费外,赠《西风》月刊及《西风副刊》全年各一份”。所以,确切地说,张爱玲获得的不是《西风》征文“第十三名荣誉奖”,而是“名誉奖”第三名。后来成为台湾著名小说家的吴讷孙(鹿桥)也确实得到了征文奖,但不是“首奖”,而是第八名。
大有争议的征文“首奖”《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作者水沫来自上海,很可能是个笔名。此文在《西风》第四十四期上随评选结果一并刊出,系作者在爱妻去世后的第二十天所作,思念殷殷,感情深挚,是一篇感人的悼亡之作。全文字数刚好是五千字,根本不存在张爱玲所说的“不计字数,破格录取”。那么,又怎么解释张爱玲关于先收到获得“首奖”通知,后又突然改为“名誉奖”第三名的指责呢?这极有可能也是张爱玲误记。她当时收到的该是获奖通知,而不是获“首奖”的通知。假定正如像她所说中途变卦,《西风》编者大可改授她第二名或第三名,或者授予她新设的“名誉奖”第一名,而不至于把她改为“名誉奖”的最后一名,这未免太不合情理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西风》编者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授予她“首奖”,而只考虑授予她“名誉奖”。至于张爱玲所说的“首奖”作者“用得着这笔奖金”,故而《西风》编者“帮他这个忙”,是否根据确凿,还是当时张爱玲远在香港道听途说?因当事人均已下世,只能永远存疑了。
《天才梦》与“名誉奖”第二名《黄昏的传奇》一同发表于一九四○年八月《西风》第四十八期。平心而论,获首奖的《断了的琴弦》虽然文情并茂,毕竟只是中规中矩的抒情文,不像《天才梦》短则短矣,却是才华横溢,意象奇特,时有神来之笔,最后一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出自二十岁的少女之手,道尽了多少人间沧桑,实在令人惊奇,也令人回味无穷。但这是文学趣味见仁见智的问题,编者评选《断了的琴弦》为第一名自有其道理,不能苛求。何况这次征文得奖作品后来结集出书时,就以“天才梦”为书名,可见编者对《天才梦》还是颇为欣赏的。其实名次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西风》借这次征文“提倡西洋杂志文体,企图在我国杂志界灌进一些新力量”的初衷已基本达到。张爱玲的《天才梦》在近七百篇征文中脱颖而出,首次在全国性刊物上亮相,意义非同一般。它昭示着一颗文坛新星已冉冉升起,张爱玲从此走上了职业写作的不归路。张爱玲晚年对此事的回忆也是耐人寻味的。回忆录最大的价值在于为历史保留下一些真实,因此,比较客观、坦然、真实地对待自己与历史,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对《天才梦》获奖经过的误记,既表明张爱玲对自身文学才华的充分自信,也表明张爱玲毕竟也是常人,她再清高,再通达,再与世疏离,仍很在乎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张爱玲一九七一年六月初接受研究者水晶采访时,就“谈到她自己作品留传的问题,她说感到非常的uncertain(不确定)”。这是值得张爱玲生平研究者和作品爱好者关注和思考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