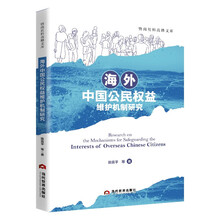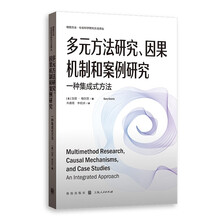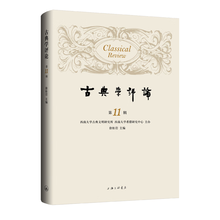市民社会淡出,国家粉墨登场将个人从社会约束中挣脱出来的趋势给民主社会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社群的消失、社会信任的下降、对权利的偏执以及无视公益而对个人意志的一味肯定。这些都是市民社会理论家会反复提及的问题。
如果政府也站在完全偏向权利一极、拒绝任何更高道德的个体一边,它就不得不去满足个体不断增长的索取欲望,这损害的往往是社群的利益。而试图不断用立法的方式推动人类进步,正是今天我们这个政治化社会(politicized society)的核心理念。
面对自由个人主义的兴起,美国法律和政治体制的应对之道就是越来越多地把一切争论都化约为不受限制的个人权利语言,用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玛丽,安·格伦顿(第十五章)的话说叫“权利话语”。当人类事务只能依靠法律和政治来裁决时,一切都变得政治化,即使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也是如此。随之而来的将是国家的无处不在,即使它的能力和合法性都在降低。
最终,实质性的宪政原则将由政治科学家迈克尔·桑德尔(第十四章)所称的“程序共和”所取代,个人得到了很多权利,却没有相应的公民意识。民主体制内的斗争将完全集中于如何调整民主过程以满足个人及团体的各种欲求,而非如何实现民主的实质性目标。
一旦所有事务都按照民主多数的原则决定,人们就不得不屈从于控制立法过程的那些人的一时兴致。法律由此堕落为政治上拥有强大组织的团体的专断工具,一个团体获得的授权就意味着另一团体必须担负的义务。法律于是不得不在冲突的派系和主张之间,寻求更理想的平衡与界限。
随着市民社会的淡去,新画面中法律和国家的色彩则越来越浓。法律由此常常被赋予双重的使命:既要确认人们的性自由,又要保护人们不受性侵犯;既要保证某些群体的性别和种族优势,又要给其他群体提供反向歧视的保护;既要保护罪犯的权利,也要保护受害者的权利;既要维护言论自由,又要以新的权利规定来对付仇恨言论带来的伤害;既要保护个人也要保护社群的权利,等等。
当然,法律本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些领域形成一种小心翼翼的平衡,但今天为了对付五花八门的权利要求,却需要法律达到一种令人恼火的精确度,这是前所未闻的。事实上,要达到这种程度的立法和谐与平衡,超出了法律与国家机构的能力。法律变成了一个忙得焦头烂额的裁判员,因为他裁决的这项运动一方面充斥了各种规则,另一方面违规的行为又仍然比比皆是——做这种比赛的裁判实在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一个公正美好社会的追求被缩减为一场围绕规则的战斗。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