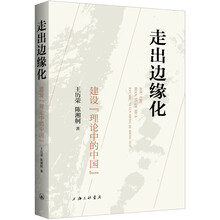这些学人集团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学生投到门下多半是人仕,介绍学生人仕似乎也成为老师的职责之一。《论语》中记载孔子“使漆雕开仕”。子路是大弟子,也可充任推荐人,“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墨子以介绍学生出仕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他对弟子说:“姑学乎,吾将仕子。”见于记载的,曾仕滕绰于齐,仕公尚过于越,仕曹公子于宋,仕高石子于卫。被仕的还有耕柱、魏越等。学生也可以请求先生介绍出仕。墨子的弟子就有“责仕于墨子”者(z)。被仕弟子对先生仍保持师生关系,要将俸禄的一部分奉献给先生,这在墨家有明确规定。如果出仕弟子表现不好,先生不仅要批评,如孔子批评冉有为季氏聚敛,号召其弟子“鸣鼓攻之可也”。有的还要召回来以示警告,在墨家中有此规定。介绍弟子出仕,并对出仕表现进行监督,反映了集团内部有一定约束关系。
……
自主性或主体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时期所依恃的根据是不同的,在近代,人的自主性或主体性是由人身的自主而定的,是一种生的权利,也就是说,人的自主性并不是依靠什么“道”而有的。应该说相反,人的自主性就在自身,选择什么“道”与自主性本身没有关系;如果说有什么关系,选择什么“道” 与做什么事一样,都是自己自主的选择,也就是说,“道”与“事”等等都是自主性表现,是自主性的证明,而不是自主性的本身。但在古代,在春秋战国时代,依据道而有的自主性或主体性,与此有原则的区别,以“道”作为自主性的前提和依据,从根本上说依然是依附性的,这同人身依附有所不同,它是一种观念依附。如果所依附的“道”是主张个人独立、个性自由的,无疑会把人带人个人独立和个性自由之地;如果所认同的“道”本身是一种依附理论或有很强的依附性,那么这种“道”就会把人带人依附或半依附之境。“道高于君”与“从道不从君”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张扬“道”,君主被放在一边;另外高举“道”的人的主体性似乎也凸现出来了。但再细分析,如果所依附的“道”本身就主张等级制与君主制,那么这种“道”把人带到哪里去了呢?这里暂不说道家,只说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的“道”。从总体上看,这些家的“道”都是等级之“道”,并是君主制的体现。
在思想史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人们在阐发、高扬“道”的观念过程中,一直向“道”注人王权主义精神。进而言之,道的主旨是王权主义。这一点被我们的许多学者,特别是被新儒学所忽视。只要稍稍留意观察,这一事实应该说是昭然的。这里我只谈三点:
其一,道对王的定位及其王权主义精神。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道无所不在,千姿百态,但影响最大、最具有普遍性的,要属有关宇宙结构、本体、规律方面的含义了。道正是在这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中给予王以特殊的定位。
宇宙结构说有多种多样,但都遵循天人合一这一总思路。《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相交而生万物,而君臣尊卑之位便是宇宙结构和秩序的一环,“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前边已经讨论过,天人合一的重心是天王合一。中国古代的宇宙结构理论无疑有其历史认识意义,然而这个恢宏结构真正能把握的部分是其下层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主体就是贵贱等级制度。王则是等级之纽。
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同时又是宇宙万物之用,即所谓的体用不二。细致分析,在不同的语境中,道、天道、地道、人道、天理、心性、礼义、刑法、道德等等无疑是有区别的,但从更抽象的意义说又混而为一体。无论是“体”或“用”,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其主旨都是为君主体制服务的。有人会说,这未免把深奥的哲学问题简单化了,其实,如果把深奥的哲学问题还原为社会历史问题,有时就是相当“简单”的。把“简单”的社会历史问题深奥化,固然是认识不可缺少的;反过来,把深奥的哲学问题还原为“简单”的社会历史问题,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体用”问题如果落实在社会历史上,难道不是为君主制度辩护吗?
道所蕴含的规律性思维方式及其所揭示的规律,在中国的思想文化中有说不尽的话题,然而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最大的、在社会生活中最实际的,应该说是社会等级制度以及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王权至上论。
其二,道的纲常化及其王权主义精神。
中国是一个宗法一王权社会,从有文献记载开始,有关伦理纲常的内容就十分突出。伦理纲常向来与政治就是一体的。伦 这一类的士人的数目,在知识层中不会是个别的。荀子说,士出仕“所以取田邑也”。又说:“今之所谓士仕者,汗漫者也,贼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惟权势之嗜者也。”荀子是在批判这种现象,不过从大量的有关记载看,这倒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官位是有限的,而求仕者大有人在,于是出现了在位与在野之间的矛盾。正如荀子所说:“处官久者士妒之。”士子们为了求得一官半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帮人当官不是为了治政,而是设法捞取财富。
荀子在其著作中批评的俗儒、贼儒之辈,就是以知识换口食的所谓知识人。子游氏之儒是不是如荀子批评的那样,另当别论。就其所描绘的形象而言,是令人恶心的:“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日:君子固不用力。”大意是,苟且怕事,没有廉耻而贪图吃喝,而且还振振有词:君子本来就不用力气。
墨子在《非儒》篇对儒生全盘否定,属意气之论,不可为准的。但文中论到一些儒生“贪于饮食,惰于作务”,当是事实。儒生一项重要任务是“相礼”,主办红白喜事。这类事不能没人操办,不过以此为职业,似乎近于寄生。所以墨子讥笑这帮人“因人之家以为尊,恃人之野以为翠。(原文作‘因人之家翠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依王焕镳校释校改)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日:‘此衣食之端也。”’大意是,倚仗着办丧事的富贵人家的威势而自以为高贵,依靠富贵人家的田野收人,作为自肥之资。富贵人家有丧事,便十分高兴,恬不知耻地说:这是我的衣食之源。这样的人难得发大财,但实在是一帮寄生物。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