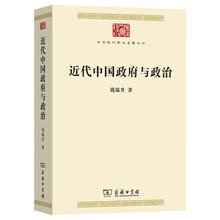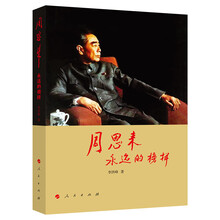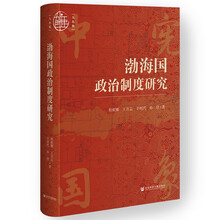更为严重的是,袁世凯1915年底图谋帝制,预备登皇极正大位,定1916年1月1日为“洪宪元年元旦”,直接篡改共和国体,名之日实行“君主立宪”,终因多方反对被迫宣布撤销“洪宪”年号,恢复共和,更不能不意味着民初始创的民主立宪政体遭遇空前的危机。至此,“辛亥革命所成之事业,仅存‘中华民国’四字矣!”②国外的不少历史事例证明,“共和国的创建和宪法的确立,可以通过推翻专制君主或随着专制君主的退位而实现。同样,篡夺政府权力的专制者也可以摧毁共和国并废除宪法。这些变化通常都伴随着暴力或暴力的威胁。”③辛亥政治革命以及民初的历史,不也是如此吗?从法律上看,袁世凯虽非篡夺政府的权力,而是依法选举的大总统,但其汲汲于威权政治、专制权力与帝王气象,却是难以否认的。正如李剑农所评说,对于《临时约法》,“袁世凯在未到必要的时候,仿佛也还肯受它的拘束;但是他的主义老早打定了,就是在实权没有完全到手以前,随你们画的什么符,他都表示尊重,若要他放弃把握实权的关键他便死也不能从了。”④这也可以解释,他摧毁共和国家,残害民主立宪政体,最终走向帝制自为,实非偶然。从提出“增修《临时约法》”到解释国会,阻挠《天坛宪草》成案,从《中华民国约法》《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到帝制自为,正是贯穿了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即以拯救民国为名逐步扩张大总统的权力,直至恢复专制政体。
民初几个震惊一时但又影响久远的典型案件或违法事件,则显示其法律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和毁损。《临时约法》公布施行半月之余,孙中山先生就给各省都督发布依法惩治越法肆行的地方长官及军事将领的命令。该命令称:辛亥革命后,“各地方行政长官及带兵将领,良莠不齐,每每凭藉权势,凌轹乡里,有非依法律辄人人民家宅,搜索银钱、衣物、书籍据为己有者;有托名筹饷,强迫捐输,甚且虏人勒赎者;有因小忿微嫌,而擅行逮捕人民,甚或枪毙籍没,以快己意者;排挤倾络,私欲横滥,官吏放手,民人无依。若不从严缔治,将怨郁之极,铤而走险,恐非地方之福。”①在与此同时发生的所谓“民国第一案”的姚荣泽案以及宋汉章案中,法部总长伍廷芳也主张:“须审慎周详以示尊重法律之意。”因为“现在共和确立,廷关于保障人民之自由,已于临时约法规定。似不应有损害民权,违背约法之事,致启人民之危惧”,否则,“民国约法之信,必因之立隳,关系不仅此案”。但根据伍廷芳的批评,身为国民党人的沪军都督陈其美,则妄为侵越横恣,“藐视司法,侵越权限。共和肇始,讵可滥用威权,至于斯极”。他还因此而忧虑当时的司法活动中出现的违犯《临时约法》的种种现象:“迩者共和确立,人民之自由权亟宜竭力保障,但闻各处官厅审讯案件,仍用刑罚,又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及至逮捕拘禁多日,尚不解赴法庭讯问判断,实属蹂躏人民之自由权,违犯《临时约法》第六条。倘不严加限制,必大起人民之惊疑,决非民国之福。”②伍廷芳之所以在一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如此强调尊重法律,是因为他知晓,在实行法治的开端,一旦治者(尤其是位高权重者)的违法行为不能得到追究和遏制,以致酿成轻法、坏法的风习,法治也就危险了。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论及保护政体的方法时指出:“对于各个要素(部分)业经调和好了的政体,最切要的事情莫过于杜绝一切违法(破坏成规)的举动,尤其应该注意到一切容易被忽视的小节。越轨违法的行为常常因事情微不足道而被人疏忽,这犹如小额费用的不断浪掷,毕竟耗尽了全部家产。由于款项不是在同一时间大笔支出,人们总觉得钱少不必计较;我们的理解有时候为诡辩谬语(谲词)所误,在这些事例上大家往往不期而都有所错误了。……‘所积聚者虽属诸小,但诸小既积,所积就不小了。’所以大家应防止在小节上的越轨违法举动的开端。”③先例一开,循者必至。善端如此,恶例亦然。因此,姚荣泽案与宋汉章案中所透示出来的信息,对于新生共和国的法治来说,乃是不祥之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