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既让J困惑,也让我困惑。这不能用J是个艺术家来搪塞了事,因为,不是只要艺术家碰过的东西就都能变成艺术品的。乔尔乔内(假设是亲手)上了底色的画布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J上了色的篱笆,不过是涂过颜色的篱笆而已。现在J意识到,只剩下一种选择,那就是直接“宣称”那个有争议的红方块为艺术品。为什么不呢?杜尚宣称一把雪铲是艺术品,它就是了;宣称一个瓶架是艺术品,它就是了。我允许J也有同样的权利,于是他宣称那个红方块就是艺术品,他成功地越过边界,就像捧着一件宝贝似的将它夺了回来。现在,我所展出的就全都是艺术品了,只不过在名分上,还有些不清不楚。尽管J的突袭取得了成功,但[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界限是什么,却还停留在哲学的晦暗中。
刚才构想的那个例子,是由一系列外形相似的副本构成的,这些副本或许带有极强的本体论色彩。很明显,也可以在哲学的语境中(即便不是在所有的哲学语境中)来构想这样的例子。接下来,我会对这类例子由以产生的原理进行关注,但也会对实际存在的例子给以同等的关注。不过,在这里,不妨再多引证一个类似的结构,期望它能为我们解除这样的疑虑,那就是以为我们仅仅是在与特属于艺术哲学的结构打交道。我要引证的这个例子来自关于行为的哲学。我引用它,并不是想表明,关于艺术的哲学从属于关于行为的哲学,我只想说,这两者具有平行的结构,实际上,在哲学分析的各个领域,都能找到这种类似的结构。我以前曾就行为理论和知识理论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平行进行过详尽说明,却也并没有因此受到诱惑,要把认知和行为等同起来。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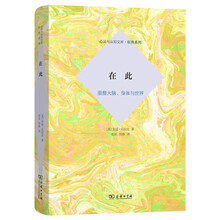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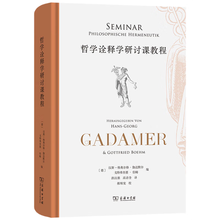



——雷尔·卡罗尔,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迄今为止最有意思的艺术哲学论著。通过定义“艺术作品”……丹托显示了广博的哲学与艺术史学识。其结果便是必将居于未来该领域话题中心的这部著作。
——马西娅.M伊顿,《美学与艺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