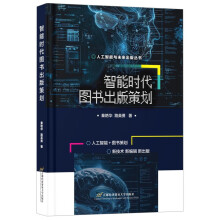与文化的灭亡竞赛——乔治·斯托金曾美其名日“救助人种学”——使得人类学家和人种学家与自然史学家之间又多了一个共同点。物种的灭亡与人们已经感受到的文化的消亡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愈加疯狂的收藏。例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就决定创办以加利福尼亚州的动物群为主题的展览,因为“加州的大型哺乳动物很快将濒临灭绝”。
戈顿这样的人种学家所面临的种群的灭绝是有其特定原因的。在写给萨拉·史蒂文森的信中,另一位来自费城的人种学家霍华德·弗内斯(Howard Furness)在谈到自己在加罗林群岛工作时所遇到的困难时,语气就不那么客气了:“那里土地富饶,作物长势喜人,却不得不为了卖钱匆忙地收割。一列列装载着这些作物出去贩卖的冷冰冰的火车几乎榨干了这片土地。那些他妈的(请原谅我如此措词!)传教士一手毁掉了当地人纯洁的头脑,硬生生地逼他们吞下智识的禁果,而我们自己早已经被这种果子的苦涩滋味折磨了千年。”
弗内斯与他的同行们正在与文明的进程竞赛,这种进程最终将到达所有像加罗林群岛那样的边远地区。对这一点,戈顿也持相同见解。在写给查尔斯·哈里森的一份备忘录中,戈顿提醒董事会主席要立刻对“落后民族”的手工制品采取挽救措施:“人类中较为先进的种族已经使自己的足迹遍及整个世界,其结果便是,那些较为落后的民族即使拥有相对发达的文明,不论其是否愿意,都将被刻上现代文化的统一烙印。而这一影响将直接造成很多在野蛮民族的风俗中得以保存的古代传统最终被遗忘殆尽,很多民族,例如中国人,都正在用自己的民族文化交换外国的风俗。”
对于这些科学家而言,社会的进步无疑是一柄双刃剑。所有的人类群体也许都将最终达到文明的境地,成就自己的历史。但是这样一来,他们也将失去自己的文化,最终败给科学。
弗内斯对弥尔顿(Milton)的再现是发人深省的。弗内斯和其他一些人种学家都认为所谓的原始人的生存状态是纯洁且没有时间概念的,因此,他们全力赶在传教士之前到达加罗林群岛。弗内斯认为加罗林群岛的居民一直保持着“纯洁”的状态,直到商业、基督教和智识的到来最终腐蚀了他们。也就是说,弗内斯和他的同行们在对异族文化探索时,都认为自己正在接触一种未经改变的文化。在这些人种学家看来,正是来自西方的影响改变了这些从未变化过的民族。这些原始人群属于人类学研究的未开拓领域,当人类文化的两个时段在此发生碰撞时,西方世界无情的进步打乱了“自然”的时间流逝。当这些文化探索者们来到某个边远地区时,他们仿佛步入了每个历史学家都曾经历的幻境:似乎在与过去直面相对,目睹过去的逝去。
为世界“原始文化”的消逝而苦恼的恐怕都是一些具有人文主义情怀、尊重甚至崇拜这些文化的人类学家。不过这同时也反映了一种更加自私的感受,即西方社会已经失去了与自己的“蛮荒”一面的关联。默温·亨利·蔡尔兹(Merwin Henry Childs)在《大西洋月刊》上就这种“过度文明”的问题向读者讲述了自己的看法,在蔡尔兹看来,人类是“感情和知性相结合的机体”。野蛮人可能受到了前者的过多影响,但是西方人却几乎完全受制于后者。生活在19世纪末的蔡尔兹以卢梭式的语言作出结论:“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根除人类的野蛮本性,而是如何运用情感的力量对其进行训练和控制,使人类的自然冲动和决断力为其更高层次的能力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蔡尔兹所说的“根除”似乎是专有所指。
在蔡尔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能够让美国人学到“自然冲动和决断力”的那些资源却正在被根除。不过,蔡尔兹和其他那些对文化消亡不无忧虑的人类学家却揭露了人类学博物馆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它们所展示的是一种以文明为顶点的文化等级。而另一方面,用蔡尔兹的话来说,也许西方世界是太过于文明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