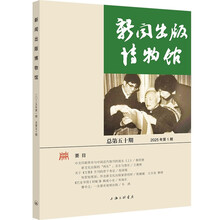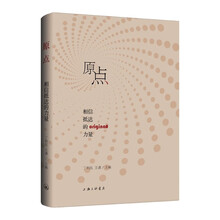对韬奋的深入研究要以韬奋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反思为切人点。能否在有关出版物上开辟类似“我与韬奋研究”的专栏,请有著述的韬奋研究者自述研究的甘苦得失,作为后人借鉴;能否请学有专长的韬奋研究前辈开设“韬奋研究前沿”的讲座或专题,或撰就相关文章,以为后来学子的指引。从中国知网的全国硕士、博士论文库中知晓,目前至少有三人以韬奋为题做硕士论文。湖南师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陈先初先生指导龚鹏撰著了《试析抗战时期邹韬奋的民主政治观》,山东师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孙占元先生指导李华撰著了《邹韬奋与中国近代新文化》,河南大学新闻学专业宋应离先生指导孟芳撰著了《邹韬奋期刊编辑思想研究》。青年学子是韬奋研究的后备军、生力军,依托高校的学士、硕士乃至博士论文是培养韬奋研究队伍、多出研究精品的有效方式。如能形成有效的引导、组织、激励方式,当会有良好结果。
韬奋是一个鲜活的存在。过去的研究更多地探究、描绘了他文化战士的侧面,其实作为出版思想家的侧面更值得关注,但要有宏阔的文化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才能有所洞察,突破目前某些表面化、平面化的研究。
应该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中国现代出版思想史的背景下梳理韬奋研究中的一些难点和重点,组织人员重点攻关。如《生活》15.5万份的发行量,不少专家都论断是当时中国期刊发行的最高纪录。如陈挥在《韬奋传》中说:“《生活》周刊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上海滩上,发行量屡创中国杂志的新纪录。”但其于中国期刊历史意义何在呢?我模糊地感觉到,在此前,深刻地影响历史进程的期刊当属《新民丛报》和《新青年》,但它们更主要的属思想刊物,影响主要在青年知识界,而《生活》则是大众期刊,影响的社会阶层不同。在《生活》之后,破其发行记录的第一个是他主编的《大众生活》,第二个就是1951年的《时事生活手册》了,那是中国期刊史上第一个发行量过100万份的刊物。北京印刷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卢芳曾力图破译这15.5万份的市场分布及其当时的市场占有率的情况,我很赞同这一研究思路。但她泡了几天图书馆后,失望地告诉我,找不到相关资料。
我多么希望是她路径不对,与潜存的数据擦肩而过。郝丹立在《邹韬奋的(生活)周刊精神》一文似乎也想探究《生活》所定位读者的规模,引用1938年中共地下党编写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的估计,当时上海的各类职员有二三十万人。这数据因时间偏离而只能作为参照。关于《生活》15.5万份发行量的成因,应该说既是一个期刊历史命题,也有相当的现实指导意义。但并不见专文探讨。有些韬奋传记就《生活》设有专章,但只随韬奋脚步记述而已,缺乏传播学理论层面的论证与分析。王畅在《编辑学刊》撰文《“永远立于大众的立场”--论邹韬奋的出版编辑思想》指出:“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史上,像韬奋这样热爱读者,重视并切实做好报刊的读者工作,且和读者保持长久和真挚的友谊的,是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与之比美的。”观察诚然符合历史事实,韬奋以如此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读者来信回复,固然出于其新闻专业出身的职业理性,出于他内心深处为民众的观念,但这仅仅是一种公益行为吗?韬奋当时不会自觉意识到出版《生活》就是当前左叫右嚷的期刊产业,但韬奋1940年很精辟地言说了出版的事业性与商业性。编辑出版《生活》时的韬奋在满腔热血的同时,未必一点没有顾及杂志的营业性。但这读者来信回复的工作对15.5万份发行量的贡献率有多大呢?四年前,我注意到《生活》读者来信和发行量同步增长的“曲线现象”,并写入了《期刊策划导论》一书中。要说读者参与和期刊发行量、期刊社会影响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典型案例也许莫过于《生活》了,但我在那书中缺乏严密系统论证,非因篇幅而是功力局限。
韬奋研究还需要国际化视野。需要在世界期刊史、世界出版史的比照中研究韬奋出版思想的同步性、先进性。比如报刊发行量公证问题,近年来有些说法和做法。邹韬奋1932年3月在《创办(生活日报)之建议》中就说:“本报为保证广告之效力计,按时请会计师检查销数,正式公布,广告价格依实际销数而随之增加。”这在中国报刊史上即使不是最早也是较早的相关文字与举措了,与美国相差也不过二十几年。韬奋出版思想与实践中类似这样与国际潮流保持同步或先进的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只是研究者挖掘不够而已。
在这次韬奋出版思想研讨会期间,我去虹口鲁迅公园参观了鲁迅纪念馆,获得的是心灵震撼。那撕破幽暗的一线灵光,那于无声处的呐喊,久久地萦绕在脑际,以至走出纪念馆,一时之间恍若隔世,茫然失语。鲁迅、韬奋,同时代人,其人格风貌、其职业领域诚然有所差异,鲁迅是民族魂,韬奋是新闻出版工作者的楷模,但能否把韬奋纪念馆请出故居,使韬奋纪念馆更具心灵的影响力呢?听说上海在筹建出版博物馆。如果难以办到,也是于理有据,韬奋一生操劳奔走皆为民众,纪念馆理当蛰居民宅之间,与民同乐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