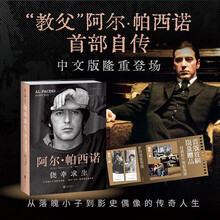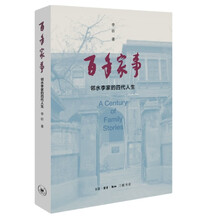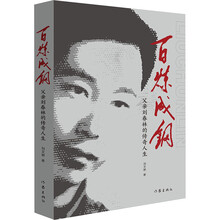第一章 挥别奥地利
我出生于饥荒年。1945年,盟军击败希特勒的第三帝国①,占领了奥地利。在我出生前两个月,即1947年5月份,维也纳因饥荒而引发了暴动。即便在我们当时居住的施蒂利亚州,食物也同样短缺。很多年后,母亲提醒我她和父亲为了抚养我所做的牺牲时,总会说起她在乡村觅食的经历:走过一个又一个农场,一点点地搜集黄油、糖和粮食。她有时候一去就是三天。他们为此发明了一个词——“囤食”,就像仓鼠囤积坚果;要知道乞讨食物在当时很普遍。
塔尔是我们镇的名字,那是个很典型的农村。几百个家庭在这里安家落户,他们的房子和农场组成自己的小村落,被乡间小径联系在一起。没铺柏油的主路在满是田野和松树林的低山上延展。
我们很少看见当时管理此地的英国军队,只是偶尔会看到卡车载着士兵呼啸而过。但是东边被俄国人占领,他们就显眼多了。冷战已经开始了,我们都很怕俄国人会把坦克开进来吞并我们。教堂里的牧师也会用恐怖故事来吓人,说俄国人会射杀在襁褓中的婴儿。
我家在山顶上的公路边,小时候我一整天都很难看到一两辆车开过。一座从封建时期保留下来的城堡废墟就在我家正对面一百码开外。
附近的斜坡上坐落着镇长办公室,以及母亲让我们去做周日弥撒的天主教堂;当地的饭庄,或者说小酒馆,是镇上的社交中心。另外还有一座小学,我和长我一岁的哥哥迈因哈德①就在那里上学。
我最早的记忆是母亲洗衣和父亲铲煤的样子。当时我还不到两岁,但对父亲的记忆却很鲜明。他是个健壮的大家伙,很多事都亲力亲为。每年秋天我们会弄到冬天用的煤,一整卡车的煤倒在家门口,这时他就会让我和迈因哈德帮他把煤抬到地下室。能当他的助手很让我们自豪。
我的父母原本都是来自遥远的北方的工人阶级家庭——大部分人在钢铁工厂做工。“二战”末期的一片混乱中,他们在穆尔祖拉格市相遇了②。我母亲奥瑞莉亚,当时是市政厅食品配给中心的文员。她刚刚二十出头,可战争却将她变成了寡妇——她的丈夫在婚后八个月就战死沙场。有天早晨,她正在办公桌前工作,不经意间注意到我父亲正在过街——看起来比她稍年长,大概三十五六,但是又高又帅,穿着地方警员的宪兵制服。她对穿制服的男人有一种特殊的狂热,所以自此她每天都会留意他。她弄清楚他的换岗时间后,就一次不落地在办公桌前守候。他们会隔着打开的窗户聊天,她会把手头上的食品分他一些。
他叫古斯塔夫·施瓦辛格。他们在1945年下半年结婚了。那时他38岁,而她23岁。我父亲被派往塔尔,管理一个四人小队,负责镇上和附近乡村的治安。薪水勉强能维持生计,但这份工作给他们带来了一个住处——一座林务官的老屋。护林人住在一楼,巡官和他的家人住顶楼。
我童年的家是个十分简单的砖石建筑,规划良好,厚实的墙壁和小窗用来抵挡山里冬季的寒冷。我们有两间卧室,每间放一个煤炉用来取暖。还有一间厨房,我们在那里吃饭、做功课、洗漱、玩游戏。母亲做饭的炉子让屋里很暖和。
房子里没有铺设水管,没有淋浴头,也没有抽水马桶,只有一个夜壶。离家最近的水井在400米外,即使下着大雨或大雪,我们中间必须有一个人去打水。所以我们的水都是省着用的。我们把水烧热,倒进脸盆,用海绵或布擦拭自己——母亲会先用干净水自己洗,然后是父亲洗,最后轮到我和迈因哈德。水的颜色变深一点也无妨,只要我们不用去水井跑一趟。
我们有一些基本的木头家具和几盏电灯。父亲喜欢收集图片和古董,但是随着我们慢慢长大,这成了他无力维持的奢侈爱好。音乐和猫让家里充满生机。母亲经常弹着齐特琴给我们唱各种歌曲和摇篮曲,但父亲才是真正的音乐家。他会吹奏各种乐器:小号、粗管短号、萨克斯、单簧管,样样拿得出手。他会作曲,还担任地区宪兵乐队的指挥——如果州里有警官殉职,这支乐队会在葬礼上演奏。夏天的很多个周日,我们都会去公园的音乐会,他会在那儿当指挥,有时候还亲自上阵演奏。他家里的人几乎都精通音乐,但是我和迈因哈德没能继承这优良基因。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养的是猫而不是狗——也许因为我母亲喜欢猫,而且它们会自己捕食,不用我们养。但是我家一直都有很多猫,屋里屋外撒欢,随时随地地卷成一团,叼着从阁楼抓来的半死耗子炫耀自己是多了不起的猎人。家里每个人都有一只猫在床上陪伴入睡,这是我们的传统。有段时间,家里甚至有七只猫。我们爱猫,但不溺爱。由于当时不流行带宠物看兽医,所以当某只猫太老或病重,我们就等着听后院的枪声——来自我父亲的手枪。然后母亲、迈因哈德和我出去把猫埋起来,竖个小十字架。
母亲有只叫穆姬的黑猫,她总是说它很特别,我们却不以为然。我快10岁的某一天,因为不想做功课跟母亲吵起来。穆姬像往常一样蜷在客厅的沙发上。我肯定是说了特别横的话,母亲准备上来给我一巴掌。我注意到了,想挡开,却用手臂打了她一下。穆姬一下子就从沙发上跳下来——它跳到我身上,开始抓我的脸。我把它扯下来大喊:“天啊!你干吗呢?!”母亲和我面面相觑,大笑起来,虽然我的脸还在流血。终于,她证明了穆姬是只特别的猫。
混乱的战争时期结束后,我父母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两兄弟能过得安稳。母亲是个身材高大、骨架子很宽的女人,她为人可靠又机智,同样也是个能让家里一尘不染的传统家庭主妇。她会把地毯卷起来,趴在地上用刷子和肥皂刷洗地板,然后用布擦干。她为之狂热的事还有把我们的衣服整齐挂好,把床单和毛巾精致地折好,边边角角跟剃刀一样锋利。她在后院里给我们种甜菜、土豆和浆果,到了秋天她会把蜜饯和泡菜放在厚玻璃瓶里准备过冬用。父亲每天12点半从警局回来,她总是已经准备好午饭,晚饭也是在父亲晚上6点回来准时上桌。
她还是家里的会计。她做过文员,所以做事井井有条,对书写和算术很在行。每月父亲把工资带回家,她会给他500先令,剩下的用来贴补家用。她处理家中所有的信件,付每个月的账单。一年一次,通常在12月份,她会带我们去买衣服。卡斯特纳乌勒商场在格拉茨市,我们可以搭公车去。那座老楼只有两三层,但是在当时的我们眼中它跟美国大商场一样大。里面有自动扶梯和金属的带玻璃的电梯,所以上上下下的时候我们能看遍商场的一切。母亲只给我们买那些绝对的必需品,像衬 衫、内裤和袜子等,这些东西会在第二天整齐地包在棕色纸包里寄到家里来。当时分期付款还是新事物,她很是中意这种每个月付一部分直到把账单付清的方式,这可以推动像我母亲一样的人去购物,真是个刺激经济的好办法。
她甚至处理家里的医疗问题,虽然我父亲才是受过急救训练的人。我和我哥把小孩子能得的病都得过了,像腮腺炎、猩红热、麻疹,她有了很多练手的机会。似乎没什么能阻止她:在我们还是蹒跚学步的幼儿时,一个冬夜,迈因哈德得了急性肺炎,当时没有医生和救护车,我母亲把我和父亲留在家,把迈因哈德绑在背上,在雪里走了两英里多的路把他送到了格拉茨的医院。
我父亲的性格阴晴不定。他慷慨而多情,特别是跟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深爱着对方,你可以从一些小细节看出来,像她给他端咖啡的样子,他总是给她买小礼物,总是抱她、轻拍她的背。我们也得以分享他们的爱意:我们总是跟他们睡一张床,特别是我们被打雷闪电吓到的时候。
但是每周都有一次,通常是周五晚上,我父亲会喝醉了才回家。他在外面待到凌晨两三点,跟一些熟人在小酒馆的同一张桌子上喝酒,这群人一般包括牧师、小学校长和镇长。我们会被惊醒,听到他气呼呼地冲来撞去,对着母亲吼叫。但是怒气一下就消了,第二天他会变得温柔贴心,带我们出去吃午餐或者买礼物给我们作为补偿。但是,如果我们行为不端,他还是会扇我们巴掌或者拿皮带教训我们。
对我们来说,这一切太正常了:所有当爹的都体罚孩子,都会醉酒回家。住在我们附近的一个父亲会揪住儿子的耳朵,手里拿一根细长棍子追打他,那棍子浸了水之后打得更疼。喝酒好像只是同志情谊的一部分,大多数情况下是利大于弊的。有时候妻子们和家人们会被男人们邀请到小酒馆一起聚聚,跟大人们坐在一起,让他们请客买小吃和甜点,让我们这些孩子觉得十分荣幸。或者我们可以到隔壁房间喝可乐、玩桌游、看杂志或者电视。我们常常到了午夜还待在那里,心想:“哇,这真是太棒了!”
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这种惬意背后的酸楚和恐惧。我们在一群觉得自己是窝囊废的男人们中长大。他们这一代发动了“二战”,却输了。战争期间,他离开宪兵队变成德国军队的警察。在比利时和法国服过役,在北非期间染上了疟疾。1942年,他差点在最血腥的列宁格勒战役①被捕。他住的楼被俄军炸毁,被瓦砾困了三天。他的背断了,两条腿都中了流弹。他在一家波兰医院里待了好几个月才伤愈出院,回到在奥地利的家,加入了民警部队。但是谁知道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他的精神创伤何时才能恢复呢?这些都是我在他们喝醉的时候听到的,可以想象这些对他们来说有多痛苦。他们都打了败仗,同时害怕有一天俄国人会来抓他们去重建莫斯科或者斯大林格勒。他们试着压抑怒火和耻辱感,但是失望已经深入他们的骨髓。想想吧,你被允诺能成为一个新帝国的公民,每个家庭都能得到最新的安置,可结果是,你回到满目疮痍的家乡,囊中羞涩、缺衣短食,一切都需要重建。在占领军的统治下,甚至你的国家都不再属于你。最糟糕的是,你没法消化你经历的一切。这些都是不应该被谈起的,但没有宣泄的出口你又怎么能应付得了这难以想象的心理创伤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