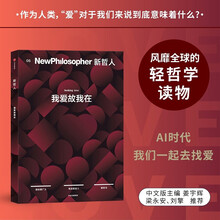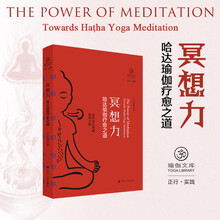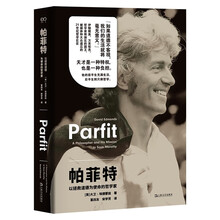我第一次见到维特根斯坦是在1938年的米迦勒节学期,那是我到剑桥的第一个学期。在一次伦理学学会的聚会上,晚间的论文宣读以后开始了讨论,有一个人开始结结巴巴地发表评论。他极其困难地表达着自己的思想,他的话对我来说是费解的。我悄声问我的邻座:“那是谁?”他回答说:“维特根斯坦。”我感到惊讶,因为从道理上讲,我料想《逻辑哲学论》的著名作者是一位年纪较大的人,而这个人看来很年轻——也许约35岁。(他的实际年纪是49岁。)他的面孔瘦削并呈棕色,侧面像鹰鹫而且很漂亮,头上覆盖着卷曲浓密的棕发。我觉察到房子里的每个人对他都很敬重。在这个不顺利的开头以后,他有一会儿不说话,但显然他的思想在紧张地活动。他的样子很专注,他用双手做出明确的手势,好像是在演讲。别的人都保持着专心和期待的沉默。后来我多次地见到过这种情形,而且认为它是完全自然的。1939年大斋节学期,我听了维特根斯坦关于数学的哲学基础的讲课。在1939年的复活节学期和米迦勒节学期,他接着讲这个题目。大约十年以后我重新研究了我的笔记,在此以前我觉得这些讲课我几乎一点也没有搞懂。尽管如此,我也和别人一样知道,维特根斯坦是在做着重要的事情。人们知道他在竭尽全力地研究一些极为艰深的问题,而且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完全是独创性的。他的讲课没有准备也没有笔记。他告诉我,有一次他试着按照笔记讲课,但是结果很不满意:那样说出来的思想是“呆板”的,或者如他对另一位朋友所说,当他开始念笔记的时候,词语就像是一些“僵尸”。在他习惯采用的方法中,他对讲课所作的唯一准备,如他对我说的,就是在课前用几分钟的时间来回想前一课中探索的进程。对此他在讲课开始时简要地概述一下,然后他从这里出发,努力用新鲜思想来推进研究。他对我说,他之所以能够进行这种即席的课堂讲授,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他对讨论中的所有问题都做了而且一直在做大量的思考和写作。这毫无疑问是真的;尽管如此,在这些课堂上进行的仍然大多是新的研究。无论是讲课还是私人交谈,维特根斯坦在说话中总是用特殊的语调来加强语势。他说着出色的英语,以一位有教养的英国人的声调说话,虽然偶尔也会出现德语化的结构。他的声音洪亮,音调比一般男声略为高一些,但并不刺耳。他说话不太流利,但是很有力量。凡是听他讲过话的都感到这是一位特殊的人。他讲话时,面孔非常活跃而富于表情。他的眼睛深沉,常常显得使人生畏。他的整个人格威武有力,甚至显得庄严。相反地,他的衣着极为俭朴。他总是穿浅灰色的法兰绒裤子,穿一件开领的法兰绒运动衫,一件紧身毛茄克或一件皮茄克。雨天出门时,戴一顶粗呢便帽,穿一件浅棕色的雨衣。他几乎总是拄一根轻便的手杖散步。不能想象维特根斯坦会穿一身礼服,系领带或者戴礼帽。他的衣服,除了雨衣以外,总是十分清洁,皮鞋擦得发亮。他身高大约五英尺六英寸,身材瘦长。他每周上两次课,每次课二小时,从下午5时到7时。他要求准时,如果有人迟到两分钟他就会生气。在他担任教授以前,上课主要在他各个朋友所住的校舍里进行,以后就在他自己的三一学院惠威尔院的住所里进行。听课的人自带椅子或者坐在地板上。有时非常拥挤。特别突出的是1946年米迦勒节学期开始的讲课,大约来了30个人,挤在一起水泄不通。维特根斯坦在惠威尔院的住所,陈设非常简朴。房里没有安乐椅和台灯,没有摆饰也没有图画或者照片,墙壁上空荡荡的。起居室里有两把帆布椅和一把普通的木椅,卧室里有一张帆布床。一个老式的取暖铁炉放在起居室的中间。一个窗台上有一些花,房间里也有一两盆花。有一个放置手稿的铁保险柜,一张他在上面写字的牌桌。几个房间总是一尘不染地整洁。班上的听众带来的椅子是三一学院的,不讲课的时候放在楼梯平台上。如果有人来迟了一点,就要引起明显的调整,因为必须移动已经摆好的椅子腾出地方来。讲课开始以后,人们必须要有点勇气才敢进去,有的人宁可走开而不愿面对着维特根斯坦生气的眼光。维特根斯坦坐在房间当中的一把普通木椅上。他在这里进行着紧张的思考。他常常觉得自己搞糊涂了,而且把这点说出来。他经常这样说:“我是一个傻瓜!”“你们的老师糟透了!”“今天我确实太笨了!”有时候他怀疑他是否能够把这节课讲下去,但他极少是在七点钟以前下课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