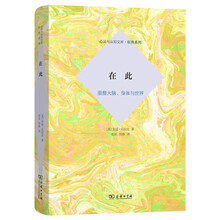没什么比把社会学遭受的命运与精神分析受到的对待(随便哪个二流作家或哲学家都通过表达他对社会学怀有的理所应当的不屑一顾,在客观上和主观上提高自己的地位)进行对比,能更好地衡量社会学的结构失信,社会学,如同一切从属于它的东西,都在知识世界中受到了结构失信的打击,社会学与精神分析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比如科学地解释人类行为的抱负。正如萨拉·温特指出的,精神分析披上了超历史的普遍性和高贵的外衣,这种普遍性和高贵传统上是赋予希腊悲剧的,希腊悲剧被学校教育传统巧妙地非历史化和普遍化了。通过把新科学纳入索福克勒斯(经典教育的至尊之一)悲剧的世系,弗洛伊德授予它学院贵族证书。拉康通过回到希腊本源,提出索福克勒斯悲剧的新阐释,他恢复了这个世系的活力,这个世系也被一种兼具马拉美和海德格尔的晦涩和大胆的风格所证明。但这只是解释作为“灵魂治疗”的精神分析与唯灵论(甚至更确切地说是天主教)的(至少表面的)相似性的因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精神分析至少在70年代的法国,处于最高贵、最纯粹的智识活动一边,总之,与社会学截然相反。作为关于民众事物的平民科学的和通俗唯物主义的科学,社会学,尤其在拥有古老文化的国家,通常被视为致力于人类生活的最庸俗、最常见、最共同之方面的粗浅分析,而它对被当做参照或对象的人文主义文化的追根溯源,远远没有产生一种博取好感(captatio benevolentiae)的作用,反而被用来增强真正信徒的愤怒的、亵渎神圣的僭越或侵犯。
法国大学过分沉浸在对知识场的文学迷恋中,并过分关注报纸的看法和认可,无法为研究者提供大西洋彼岸自主的和自足的大学场所保证的东西,这个大学场具有不同学科的专家的严密网络,既灵活又严格的科学交流形式,研究班,非正式研讨会,等等。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