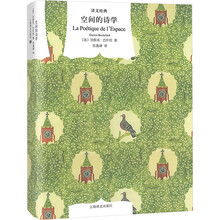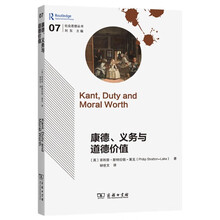11.在特定的现代文化概念的意义上——此处,暂且不论严格地讲在现代文化概念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文化概念——,霍布斯把文明状态(status civilis)理解为自然状态的对立面,文明状态成为所有狭义文化(即所有艺术和科学的教养)的前提,而且它自身以另一种特定的文化为基础,即以人类意志的训练为基础。在此,我们暂且不论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与文化(广义的文化)之间相互对立的看法;在此,我们只强调一点,即霍布斯完全把自然状态描绘成战争状态,不过,我们必须记住“战争的天性并不存在于实际的斗争中;而是存在于众所周知的另外的倾向中”(《利维坦》第十三章)。在施米特的术语中,这种表述意味着自然状态是真正的政治状态。因为,施米特同样认为,“政治”并“不存在于战斗本身当中……而是存在于这种现实可能性所决定的行为之中”(页37)。由此看来,被施米特视为基础的政治就是支撑所有文化的“自然状态”,施米特恢复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概念所具有的荣耀地位(参见页59)。由此,那个必须规定政治特有的划分的分类问题也有了答案:政治乃是人的状态;事实上,政治这种状态乃是人的“自然的”、根本的和极端的状态。12.事实上,施米特对自然状态的界定与霍布斯有着根本差别。在霍布斯看来,自然状态是个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而在施米特看来,自然状态则是群体(尤其是国家)之间的战争状态。对霍布斯而言,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敌人;而对施米特而言,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定位于朋友和敌人的划分。这种差别植根于霍布斯自然状态定义的论战意图:既然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那么它就可望激发人们摆脱自然状态。施米特则以政治状态反对这种对自然状态或对政治的否定。13.在霍布斯的思想中无疑存在着对政治的全盘否定。[224]按照他的学说,自然状态至少在国与国的关系中仍然存在下来。因而,霍布斯把自然状态抨击为个人间的战争状态——施米特无疑采纳了这种观点,他的论述表明,在保护与服从的关系上,他明确地追随霍布斯(页53;另参见页46以下)——并不需要对施米特意义上的政治,即人类群体间关系的“自然”性质提出质疑。然而,按照施米特,政治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可以“要求……自己国家的成员随时准备牺牲”(页46)。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