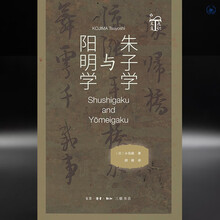治身即修身,属于道德修养范围;事君即政事,属于事功的范围。叶适认为这两者是一个想修成“君子”的人的最高境界(极行)。如果在修身时从小事上严格要求自己,在政事上能识大体、顾大局,这就离君子人格不远了。在治身与事君二者的关系上,叶适认为有本末、先后的区别,他说:“于治身之谨诚细微无不尽焉,则推而达之,固所以合乎人伦之大义也,岂非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而非偶然幸致者乎!”①也就是说,如果能在治身上谨慎修养,无纤毫过失,然后将这一品德推而达于政事,就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目标,亦即治国、平天下。治身是本,是先;政事是末,是后。这其中的轻重缓急、铢两轻重,是十分清楚的。
叶适还在《答省詹书》中明确说:“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宾主之大伦也;慈孝、恭敬、友悌、廉逊,忠信之大节也。”君臣、父子、夫妇、朋友、长幼,是为“五伦”。自帝尧令皋陶掌教,务明人伦;孔子提倡弟子入孝出悌、忠信礼敬、仁民爱物;孟子重申“孝悌忠信”、“仁义礼智”,明确要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有信,长幼有序”,于是重视伦常教育、提倡忠孝仁义,就成了儒家的重要特色之一。叶适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旗帜鲜明地将“五伦”和“孝悌忠信”等道德观念作为人生的“大伦”和“大节”。在他看来,这些大伦大节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是否自然而然地得到贯彻和执行的事情。他说:“所谓豪杰者,卓然兴起,不待教诏而自能,不待勉强而自尽,通达无间而可以显仁藏用者,故孟子谓不待文王而兴,此某所以愿望于朋友。”②
正是出于对儒家孝悌忠信观念的坚信和自持,叶适对《老子》非毁忠孝的言行明确地提出了批判。他针对《老子》“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的观点,说:“和则不待孝,治则不待忠,其道或然矣。”这或许是初民原始的纯朴状态,但是在后来人类的知识进化、道德退化的演进历程中,这一状态只有作为理想残存于人类的记忆之中了。
面对不和不治、不忠不孝的现实,我们应作何认识,如何评判和处置呢?是怨天尤人,无所作为,消极对待,还是积极有为,提倡忠孝,复归和治呢?或是本末倒置,将不和不治反而归罪于忠孝呢?显然老子属于后者,他本末倒置地将不和不治的社会现实归罪于忠孝了。儒家则反是,处理不和不治的态度是用忠孝来加以治理。叶适正是继承儒家的忠孝观,他批评老子说:“然其所以不和不治,岂为忠孝者致之哉?若舜父母、箕子之君,并以不和不治者集于其身,又将奚咎?老子谓因废道有仁义,因智慧有大伪,而谓家国之乱亦因忠孝者致之,故欲绝焉。噫,未有不察事而可以知道者,是恣其私说而以乱益乱,非亡灭不止。悲夫!”③认为老子是单凭主观愿望(灭仁弃义、绝圣弃智)出发,任意发挥自己的一家私言,不考察事物出现的真正原因,颠倒因果,用一种衰乱的方法来对待混乱的社会,非导致天下大乱、政权灭亡不可!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