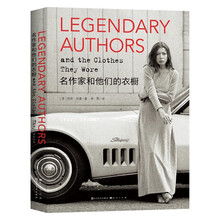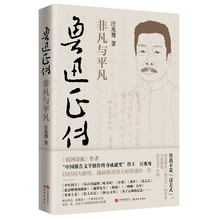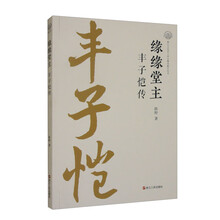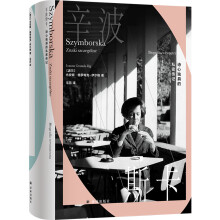作为取士的法则,八股科举在明清时代,为全社会趋之若鹜,被众多的人顶礼膜拜。在《儒林外史》中,周进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鲁编修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捆一掌血。”马二先生说:“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高翰林贬斥杜少卿:“他果然肚里通,就该中了去!”又道:“征辟难道算得正途出身么?”庄绍光奉诏进京,“把教养的事,细细做了十策”,皇帝说他“学问渊深”,问太保公:“这人可用为辅弼么?”太保公说:“庄尚志果系出群之才,蒙皇上旷典殊恩,朝野胥悦。但不由进士出身,骤跻卿贰,我朝祖宗无此法度,且开天下以幸进之心。”庄绍光因此被“允令还山”。萧柏泉奉承庄绍光道:“老先生抱负大才,要从正途出身,不屑这征辟。今日回来,留待下科抡元。皇上既然知道,将来鼎甲可望。”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八股科举在当时社会,作为一种朝廷的制度,不仅决定了广大士人的命运,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然而,八股科举所培养的八股士子,不讲学问,知识贫乏,治世无术,不讲道德品行,为人卑劣,行为不端,诸多的客观事实,恰恰成为一种尖锐的讽刺。
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宗旨并非骂世,旨归在疗治士林痼疾,所以,对那些被功名富贵扭曲了灵魂的读书人,他更注重揭出使其扭变的社会根源,最终将批判锋芒对着社会世相,指向八股取士制度。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