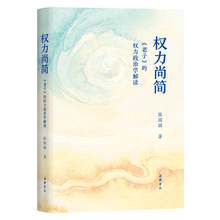韦尔斯氏与丘浅氏皆今之号善论者,韦氏以博爱联合世界为旨,然又知游牧、定居二类之必争,而谓定居之民赖游牧之侵犯而起其惰。丘浅氏则倡人类下降说,谓自由平等之说乃服从性减退之征,此性既减,不能协力一致,人类多内争而无外御之力,将日就衰亡,是不可救。然又谓今日不可不言自由平等,不言则今日无以竞存。二人之乐观、悲观大殊,而其说皆自为矛盾,韦氏之说犹为世之言泛爱者所称道,丘浅氏则囿于生存竞争之说,谓人之团体本始于争,个性一伸,不外争而内争,永无和平之曰,而不信同情之实有。其说偏宕,为众所非,然其指自由独立为分争之端,谓团体愈大则其结愈弛,则不可诬也。夫生物学者之论人道羣道,其见亦不一,而世谓人道羣道当求之生物学者,以其言足以见自然之情(此情字本《易传》,所谓天地万物之情,谓其实状),以为当然之准耳。是固不谬也。然而吾有不敢信者,以生物学之深刻者习观一切生物,等观一切生物,遂往往以物概人,以物道概人道,若古所谓同人道于牛马者,彼丘浅氏固以此自鸣之一人也。然观其所言,则每适足示人之异于禽兽,如上所引是也。由韦氏之言,则知人之异于禽兽在于有家庭,由丘浅氏之言,则知人之异于禽兽在有阶级,盖人之身体复杂,须长久养育,固不能反于爬虫之无家庭,而其智力参差,不止依本能而生活,须赖教育领袖,亦固不能效蜂蚁之无阶级,是事实也,非哲人之玄想也。是凡为人类者所同也,非有东西之异也。是自然之情也,非由少数人之私心所造以为己利也,甚明白矣。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