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企业资本主义的推崇者不得不去考虑其经济政策的社会影响,因为他们需要一种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源自于社会对企业资本主义的需求意愿超过其社会主义对手。冷战过后,,西方弱势群体似乎并没有革命性的选择,因此,尽管存在不公平,但新的领导阶层假定了人们对消费社会的认可,而不需要通过福利政策赢得这种认可。关于冷战镜面效应的一个有趣例子发生在芬兰,在那里,长期与社会主义较量的资本主义模式中诞生了一些有史以来最为先进的福利机构,而在苏联社会主义崩溃后,这些机构迅速瓦解。
而且,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曾一度被政党用于为社会主义的缺陷辩护、认为其仅是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的“转型”这一修辞具有讽刺意味地被运用到了其对立阵营。现在,莫斯科和其他地区的穷人和受压迫者正在被无家可归、疾病和饥饿夺去生命,但冷血的领导者却告诉他们,在向成熟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苦难是必需的,而新自由主义激进政策的目标正是缩短这一过程。毋庸置疑,拥有丰富气、油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俄罗斯新富大亨表现出了对企业掠夺的钟爱有加,而他们囊中的财富数额其实就是掠夺本身。
正是因为这些历史事件,新自由主义将自己看做最优和唯一可能的选项,因此表现出典型的垄断型意识形态才有的傲慢自大。其经济政策中的双重标准就是这种傲慢的最好例子。例如,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法律在坚持一系列的保护主义政策(如禁止从加拿大进口药物)的同时却鼓吹开放市场,允许商品和资产跨国流动。
最重要一点是,这种高度的自信和自傲滋生了一种普遍性态度,它否认具体情况应具体分析。新自由主义致力于继续扩张其能够提供最佳可能发展模式的普遍性言论。普救说和双重标准在法治进一步展开的概念中得以显现。在追寻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过程中,法治被认为是一种普遍性的细化法律系统,它对威胁产权底线的个人加以严格控制,而对企业行为则置若罔闻。强者主导了对弱者的控制,这既表现在国内政府与个人的关系上,也表现在国际间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上。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借助协议的权力变成了全球立法者,从而成为实现新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浪潮的理想工具。一旦它们自身开始转变,里根/撒切尔革命就演变成了一种机制实践——自然的、普遍的,且是反对党力量不可触及的。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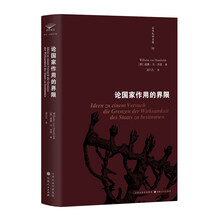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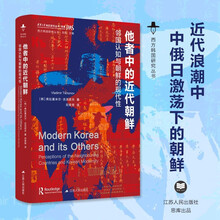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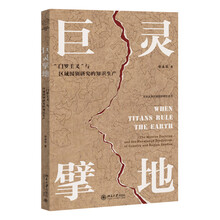





——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资本主义的灵魂:走向道德经济》(Ihe Soul of-Capitalism: Opemng Paths to Moral Economy、的作者
这是一本充满战斗性和勇气的著作,在两位作者广博的实际经验和理论视野下,该书独辟蹊径地揭露了法治的阴暗面。
——乔治·比沙拉特(George Bisharat),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纵览从殖民主义时代到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全球进程,为我们认识法治的“阴暗面”提供了开放性视角。
——萨莉·恩格尔·梅里(Sally Engle Merry),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