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詹姆斯·密尔对于非欧洲文化的论述沿袭着一种一贯的方式。他认为这些民族之间没有区别,因此所有的非欧洲人,从南海岛国的游牧民族到中国的各个民族,不管有关他们特有的生存方式、治理方式以及艺术和行为曾有怎样的评价,终归摆脱不掉“粗鲁”或者“野蛮”的定位。从他的写法看,似乎每一个能表明其劣于欧洲文明的部分都是展现本质的,而每一个反映其精致性的部分都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具有误导性的。①
此外,密尔的推测性历史的实践,与最为精细的苏格兰的推测性历史学家的实践有区别,其不同在于,他坚持将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看做主要是认知的发展。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斯密、弗格森以及米勒坚持这样的观点:即所有人在理性上都是平等的--平等地拥有洞察力、预见性以及创造力--并且坚信不同的制度反映了对不同经验的理性回应。尽管这些思想家们承认某些习惯或者法律或许会导致行为在早已失效后继续存在,不过他们并没有把这种事实看做是社会成员智力缺陷的表现。相反,詹姆斯·密尔反复指出,总体上野蛮人的行为,尤其是印度人和中国人的行为(他写作中最为详细的对象)表明了他们思维的愚鲁,认清自己利益能力的缺失,以及他们的理性屈从于冲动和激情。譬如,尽管未开化的人迫切需要发展出有关解决资源争端的手段,但是所需的结构只能在长期遭遇困难之后才能出现,想来是因为“人类缓慢的进步,是由处于原始和无知状态下的理解力所造成的”(HBI2:123-124)。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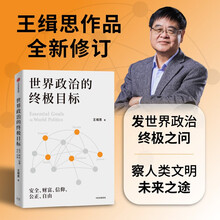








——《选择》( Choice)
每一页都体现了研究的深度、通俗易懂的文风和敏锐的才思,该书是一个布局均衡且天衣无缝的整体,揭示了帝国对于现代自由主义起源的影响。它不仅对政治理论家来说是一部头等重要的著作,对哲学、历史及文学读者而言也同样如此。
——大卫‘阿米蒂奇,哈佛大学,《大英帝国的意识形态起源》(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的作者
这本内容丰富、促人思考的著作,审视了一个目前在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及欧洲历史等领域都令人极感兴趣的主题。它值得并且应该得到广泛的阅读。其中的学术研究既细致八微,又令人信服,而皮茨的行文也引人人胜。随着分析的展开,希望理解何种因素导致某位理论家拒绝或支持对外征服的激情,既推动着皮茨的叙述,也令读者欲罢不能。
——谢里尔‘韦尔奇,西蒙斯学院,《自由与功利》( Liberty and Utility)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