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下略):您当时对京戏也很感兴趣吧?呵呵,我知道,您说北京人都喜欢。
梁(下略):我那时候啊,我这个人哪,——北京话叫做“别扭”。我父亲、我母亲、我哥哥,他们都爱听戏。我就说你们爱听戏,我偏不听戏,呵呵。那年说这话的时候也都有20岁。后来到24岁那年,从前叫民国六年(1917年),民国六年北京的政局有个新局面。怎么说有个新局面呢?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没做成,之所以没做成的缘故是西南反对他。西南——在云南不是有一位将军叫蔡锷,有唐继尧,有广西的陆荣廷,他们都反对袁世凯做皇帝。袁世凯的部下也有一个很正派的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叫做段祺瑞。袁世凯想做皇帝,他就把原来国家的制度改了。国家的制度原来在总统之下有国务院,国务院有国务总理。袁世凯想做皇帝,他就把它改了,不要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一个政事堂,他就是总揽大权在总统,不愿意另外要什么国务院、国务总理。段祺瑞反对这个事儿,但是那时候在袁世凯政府里头,他也不是国务总理,他是陆军总长,实际上军事大权由他掌着。所以旁人捧袁世凯做皇帝,他却公开地反对。
公开反对反对不了,大伙儿还是都捧袁世凯做皇帝,他就辞职——我不做官了——他不做陆军总长了,他退隐了,北京有西山,退隐到西山 上,闲住起来。他自己称病,辞职啊,辞那个陆军总长,就说我有病。袁世凯也无可奈何,他一定要辞职,要不干,也无可奈何。这样对他们北洋军人倒留下了一个生机,就是袁世凯死了,袁世凯是总统,副总统是黎元洪。按照宪法,应当由副总统接任总统,该是黎元洪出来了。黎元洪就把段祺瑞找来了,让段祺瑞做国务总理,就把原来袁世凯的政事堂那套东西废除了。黎元洪当总统,段祺瑞是国务总理,恢复了国务院。这时候南方反袁的觉得他们这样做合法,合乎原来的民国宪法,就承认他们,组织南北统一内阁,组织一个政府,这个政府一方面有北方的,另一方面也有西南反袁的,就叫南北统一内阁。这个时候按旧的说法叫民国六年(1917年),南方就推出人来参加北京的南北统一内阁,参加的人是云南的,西南方面的,是云南的张耀曾,他刚好是我母亲的一个弟弟,不是亲弟弟,一家的弟弟,我管他叫锫舅,他的号叫张镕西。他就出来担任南北统一内阁的司法总长。他平素就喜欢我,叫我给他当秘书。
他人那个时候已经在北京了吗?
他从云南来呀。
从云南来的,他本来不是在北京的。
在袁世凯还没有称帝的时候,他在北京大学做法学教授。他是留日的,在日本学法学的,反袁的时候就到云南去了。他本来是云南人。
他不但是在北京长大的,也是在您家……
是我们家的亲戚啊,我母亲的堂弟。
他在北京教书的时候,在去云南以前,您和他常常有来往吗?
当然。
您当时对佛教是最感兴趣的,那张先生呢?
那他倒没有。因为我跟他的亲戚关系,北京说法叫外甥。他岁数大过我,大得也不太多,大九岁。那年他做司法总长,我24,他33,也很年轻。
很年轻啊,做部长,当然年轻的。
他就让我给他当秘书。为什么要我给他当秘书呢?因为他是代表西南反袁的势力来的,他常常要跟西南方面的主要人物通密电。他让我掌握密码电本儿。去电哪,来电哪,去信哪,来信哪,我都管这事儿。
所以他请您是他信任您的意思,这种工作绝对不要别人知道的,您是他的亲戚,也不一定是跟您的学问有关系,主要是您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沈钧儒先生也是做他的……
就是这个时候。我是四个秘书中的一个。
哦,一共有四个秘书。
他是司法总长啊,有四个秘书。沈老师一个,我是一个,还有一位姓习,另一位姓杨,姓习的、姓杨的都是云南人,沈老是浙江人。四个秘书分担不同的任务,云南人姓习的、姓杨的管公事,他们管来往公文’,来的公文他们看,他们加意见,发出去的公文也归他们管。我专管机密的,呵呵,写点儿私人的来往信件。我把信写好,给镕舅看,末了他签个名,翻有密码的电报给他看。这年我24岁,沈老42岁,大我18岁。
这个时候的政局跟过去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必须要点明。过去主要是一左一右两党,左边就是以孙中山先生、黄兴、宋教仁为主的国民党,是从中国同盟会改组的,是偏“左”一边的。偏右一边的叫进步党,进步党的实际领袖是梁启超、汤化龙,还有林长民等其他人。本来是这么一左一右两大党。前一段是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后一段是他死了,大家反对他,他做不成皇帝就气死了。现在一切嘛都恢复,按照宪法啊,原来的宪法都恢复,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大总统,把段祺瑞找出来恢复国务院,请段做国务总理,这是民国六年(1917年)。
张耀曾代表西南方面的反袁势力参加了南北统一内阁。也就是刚才说过的,四个秘书——我主要的给他掌管一部分的事情。沈老呢,是对外的事儿。所以对外——刚才不是提过了,一个国民党,一个进步党。大家都不讲这个,制定宪法的任务给耽误了,大家一定要抛除了党见,要制宪第一,把宪法搞住,因为是制宪第一。议员合起来有八百多人,也不能散,不能完全没有组织,各自组合起来,有的叫宪法研究会,有的叫宪法讨论会,有的叫宪法商榷会,都是研究宪法的。有名的是宪法研究会,主持人是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以梁为首。后来口头上、报纸上常说谁谁是“研究系”,就是说他是宪法研究会那一派的人。
可是两院议员有八百多,有些没有收纳到这里面去,有的就叫“丙辰俱乐部”。为什么叫丙辰俱乐部呢?因为这一年是丙辰年。我们广东有个留学德国的,叫马君武,是丙辰俱乐部的头脑。还有一个有名的议员叫褚辅成,他们是“宜友社”。除此以外,分别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组织,这个时候,张耀曾跟他的云南同乡李根源,还有一位国民党老资格的叫钮永建、谷钟秀,他们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团体叫“政学会”。我们四个秘书中的沈钧儒代表张耀曾忙着招呼政学会的事儿,沈老人身体不高,头很大,留胡子。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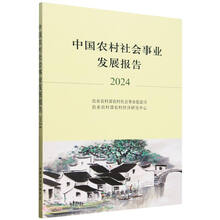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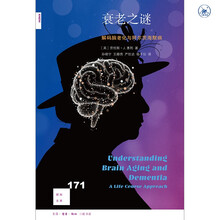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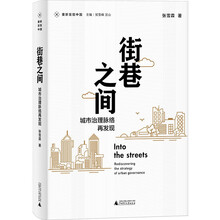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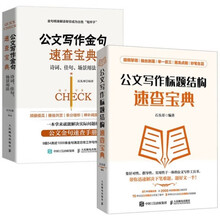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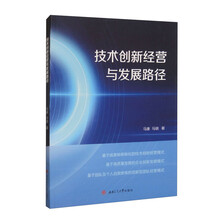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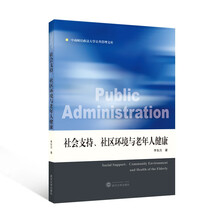



——费孝通
“我对梁漱溟非常佩服,有骨气。我佩服的人,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
——季羡林
“梁漱溟是现代中国最具特色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他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极具风骨;不尚空谈,而且能身体力行。这本《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是最早全面研究梁漱溟的美国教授艾恺与梁漱溟访谈的实录,粱老畅叙平生,艾兄如实记录,全不加修饰,极具史料价值,谨此推荐,读者不可错过。”
——汪荣祖
“梁先生有些类似于甘地这样的圣者,通过自己的不断奔走感化大地,于改造人生与社会中践履一己的感悟。实际上,梁先生自己就曾不止一次说过,儒家孔门之学,返躬修己之学也。”
——许章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