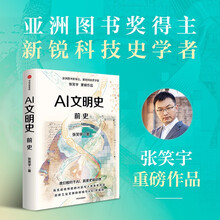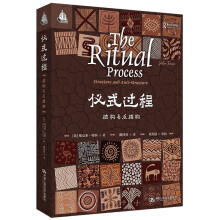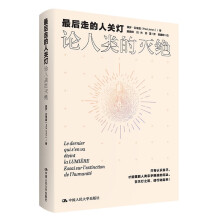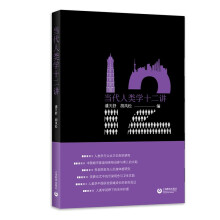如果与美国社会学家戈登用于衡量族群融合的理论模型中的7个主要变量进行比较①,那么族际通婚、语言融合、认同意识、道德规范这4个方面是与戈登提出的变量相一致的,戈登的其他3个变量(偏见意识、歧视行为、相互渗透或结构同化)可能是由于中国历史典籍中缺乏直接的相关资料,没有进入王桐龄的视线。另外西方社会学在实际调查中所关注的居住格局(是杂居还是隔离,反映了族际间相互接触的客观条件)和人口迁移(从本族传统居住区迁入其他族群居住区),作为当权族群在促进或阻碍族群交往与融合的主要政策内容,得到王桐龄的特殊重视,故把“杂居”作为衡量各朝代族群融合的专题。当然,王桐龄这里所讲的“杂居”实际上更重要的内容是当权族群为了达到“族群杂居”目的所安排的各族人口的跨地域迁移活动。<br> 近代西方欧美国家在服装式样上不断趋同,来到美洲的欧洲移民在“易服色”方面不存在重大问题,所以戈登从未提出“易服色”作为衡量族群融合的变量。而在清朝及以前的中华国土,农耕族群、游牧族群、山地族群由于自然环境、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各自的“服色”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就中国国情而言,“服色”确实应当做为衡量族群文化融合的一个变量,这从一些皇帝对于“易服色”所给予的特殊重视也可体现出来。<br> “更名改姓”在重视血统和实行祖先崇拜的中国族群特别是汉族当中,是一件非常带有象征性意义的大事。尤其是汉人改“胡姓”,更是有悖于儒家传统,不但家族断了“香火”,而且背叛了族群。西方各国之间固然也有传统的家族姓氏,但在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各国的姓氏都在流行,非欧洲的姓名让美国人在发音上有些困难,但仍然可以接受,所以美国的族群社会学没有把“更名改姓”作为一个衡量族群融合的变量。而在历史上的中国,这确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大事,而且“改名不改姓”和“改名亦改姓”之间还有差别。<br> “养子”由于在社会上人口数量相对较小,往往为人忽视,其实这种方式应当是血缘融合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帝王或贵族中收养是常见的现象,隋代靠山王杨林有十三太保,“皆为其养子”,安禄山为唐明皇养子,“晋王(李)克用之养子甚多,后唐庄宗之大臣中,赐姓名受养子待遇者亦不少;其中多数为汉人。……养子最易乱宗,亦最容易混合。……外族人为汉人养子,当然化为汉族。”②王桐龄关注各朝代发生在族群之间的“养子”现象,并根据历史记载开列出来,作为衡量当时族群融合的一个变量,应当说是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思路。<br> 在1934年西方社会学尚未系统地对族群融合的具体方面进行分类时(戈登的著作发表于1964.年),王桐龄即试图提出以上分类方法,并根据中国历史上的实际国情提出一组具有中国特色的衡量族群融合的变量,应当说具有很大的贡献。特别对于中国的族群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建设,在今天仍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六、三本《中国民族史》之比较<br> 下面试图把本文中涉及较多的由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于20世纪30年代分别撰写的三本《中国民族史》在几个方面做一下比较。<br> 1.结构<br> 我国近几十年来出版的中国民族史著作,大致有两种体例。第一种以王桐龄先生的这本《中国民族史》为代表,以历史分期为章节,在各历史时期分析各族群的交往历史。1990年江应棵主编的《中国民族史》①、1994年王钟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②和1996年田继周等撰写的《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④大致延续的也是这一体例,这三套书均以历史分期来划分各编(章),在各编(章)中分别叙述各族群之间的交往与演变过程。<br> 第二种是全书按族群分章节,从其起源讲到演变、消亡,并讨论其各个支系的变迁,吕思勉、林惠祥两位在30年代各自出版的《中国民族史》是这种体例的代表。吕思勉先生这本书的结构,在“总论”之后,即分为12章对12支族系分别叙述,在书中对于各个族属的起源及历史演变,根据各种史书典籍,分别加以考证和讨论,对于不同族系之间的关系,也努力做出清晰的交代和说明。在某种意义上,吕思勉这本书写的是这些族群各自的历史,而王桐龄写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族群交往融合史。<br> 除此之外,黄烈先生把中国古代民族史划分为唐以前和唐以后两个历史阶段,他的《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④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按族群分章节,下编则着重讨论族群交往融合的专题⑤,在体例上大致介于以上两种之间。<br> 2.分期<br> 王桐龄先生对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以汉族为主线,再把汉族发展的全部历史划分为一个胚胎期、四次大蜕变和四次蜕变之间的三个修养期。这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为林惠祥所接受,林先生也认为“中国诸民族的主干实为华夏系,其他诸系则渐次与华夏系混合而销灭其自身,或以一部分加入而同化于华夏系,保留其未加入之一部分”。他认为,“民族史上之分期实可以各民族之每一次接触混合而至同化为一期,……每一期之终亦即华夏系之扩大。准此以论中国民族史之分期可分为(1)秦以前,(2)汉至南北朝亡,(3)隋至元亡,(4)明至民国”。①林书的分期与王书的分别即在于忽略了“汉族胚胎期”,而且把王书的各个“汉族修养期”归并到四个“蜕化期”。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一书的结构,作为总论的部分分为“中国民族之分类”和“中国民族史之分期”两章,其余16章则依照中国古代族群的16个“系”分别叙述其各自的历史演变过程,全书的结构基本上属于上面所说的第二种,但由于有了讨论“分期”的一章,多少兼顾了历史分期和各族历史演变的完整讨论。<br> 费孝通教授在1989年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认为“夏商周三代正是汉族前身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从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在春秋战国的五百多年里,……是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育成时期”。②这与王桐龄提出的“汉族胚胎期”观点相一致。费先生的这篇文章也是对中国民族史的一个综述,其核心观点是分析“中华民族”如何分阶段、分层次地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多元一体”的结构。王、林两位对于中国民族发展史都持“族群融合论”和“汉族主干论”。与他们有所不同的是,费孝通教授注意到了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个从“地区性的多元一体”向“整体性的多元一体”的过渡阶段。③具体地说即是从秦汉至明朝大致地存在着中原农业地区和北方牧业地区的两个局部的“统一体”,两者之间不断接触拉锯,元朝曾短暂地建立了两者的“大一统”,但直至清朝才真正地把这两个局部统一体牢固地汇合起来。<br> ……
展开